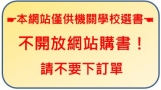厭世的凡一與放浪的一凡,
在命運的安排下,互相激盪,追尋生命的意義。
「對於生命無感而可能只好自我了結的凡一,自己的價值在哪裡?」他是凡一。
「感情關係上呈現無政府主義的一凡,或許在內心精神上是一種虛無主義吧。」這是一凡。
一場又一場的夢境,會把青年帶向何處,
透過夢的解析,可以得到「我是誰」、「如何得到快樂」、「生命的意義何在」嗎?
以及,人生終極的目標是什麼呢,必須透過湯瑪斯?曼的小說,華格納的音樂,聖杯傳奇與希臘哲人,來關照生命的真相。
自由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如何塑造台灣的命運共同體?
這是台灣人共同的使命嗎?
台灣的美食聞名全球,媽祖遶境刻劃土地情深,泰雅的祖靈在召喚,斷頭的石碑是奉獻者的精神,
這些都是銘刻台灣文化的內涵事件,是一場無盡的饗宴,還是魅影縈繞糾纏?
繼《少年凡一》、《彩虹麗子》後,藤原進三的第三部小說。主角凡一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就讀,卻無法融入校園生活,課業糟糕,不能跟上學校的步調,經常有挫敗厭世之感。一次到台灣旅行,剛好遇到心儀的教授在台灣做選情觀察研究,在教授的要求下完成測試並決定到台大當交換學生。接待他的台北寄宿家庭中,剛好有跟他同年齡的台大法律系學生一凡,兩人同一個屋簷下,展開探索台灣、追問生命意義的旅程。期間,凡一與一凡經常為夢中的景象所困擾,經由一凡母親立虹的牽引,將困擾的夢中情景寫給不在家的父親,每每都能得到一凡的啟發,了解生命的意義。
這兩位年輕人除了為夢境所擾,在台灣的生活卻豐富多采又緊湊,週間在台大求學,交朋友,每個週末都會有立虹為他們準備的早午餐,來自台灣各地的豬腳、糕餅、麵線各式美食,一凡維持每個週末到武塔當課輔小老師,凡一跟進,他們在此與到完全不同類型的人,生活方式,瞭解到台灣原住民歷史與困境。
這部小說卻不止於圍繞著這兩位年輕人,作者創造了另一條貼近社會時事的故事,也是追查台日情節的線索,翻開台灣日本時代、國民黨政權帶來的移民,所交織的族群問題。
這是一本恢弘博雅的成長小說有凡一與一凡、父與子、華格納與湯瑪斯.曼,也有死亡VS.生命、自由VS.愛、故鄉VS.旅人(犯人)、日本VS.台灣。鏡像對立映照,故事血肉題材的演奏描繪,有些是伏筆和揭曉,有些則是隱喻及象徵。
〈自序〉
在主導動機的樂聲話語中拷問靈魂
我寧願什麼也不說,也不願說得微弱。
--米勒(Jean Michelet)
這是一個父親寫給孩子的故事。橫亙在父與子的關係之間,進行著生命的凝視,聳立在前的是世代相對的巨大歧異。依稀記得我這一代人,年輕的時候,似乎多數是再怎麼樣也要拚下去的不惜掙扎;可看著、聽著當前的年輕世代,茫然中又具體明晰地漫佈著一股寧可棄世也不願低頭的倔強,這種氛圍態度,令我驚慌到甚至戰慄不已。
我們到底造就出了什麼樣的生存環境,讓年輕人將厭世當做一種選擇?這迫使年少心性趨向離世的生命困局、世間處境,是怎麼構陷出來的?
死亡,做為一個命運或抉擇的課題,終究還是得在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發現過程中,去尋求解答吧!若能找得到那即便只有希微渺弱的一點點,就像天空中垂降下來的一根蜘蛛絲,說不定還是有攀附而昇、超脫救贖的機會。不然就只能淪落幽暗了。
就算僅有一絲絲的光明、一些些的希望,還是得朝著那光明與希望的縫隙盡力而去,生命才能有超越的機會。這不應該只是我、或像我這一世代人的思維,而是跨越世代生而為人共同的信念才對吧。想對孩子說一個這樣的故事,怎麼樣在不失批判性精神的同時,能夠以一種比較具有包容性的立場與觀點,去觀照省思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這塊土地、這群人們。這堂而皇之的嚴肅主題,甫一觸及,立即在我腦中浮現的表現形式與意義典範,就是湯瑪斯?曼(Paul Thomas Mann)這位德意志最重要、最偉大的文學心靈創作者。
湯瑪斯?曼有多重要?有多偉大?兩位文化觀察╱理論名家苔雅?朱恩(Thea Dorn)和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最新出版的《德意志靈魂》(Die Deutsche Seele,台灣譯名:《德國文化關鍵詞:從德意志到德國的64個核心概念》),這部厚達九百頁的鉅著,以六十四個文化行為、現象、傳統、典範、創造領域,完整、豐富、深刻,而且批判地呈現、解析了德國文化的內涵、精神、本質,以及獨特性。作者在書中開列了兩份權威性無可挑戰的清單:「二十世紀十部最具實驗性的德語小說」、「二十世紀十二部最重要的德語長篇小說」,只有一位文學家同時名列雙榜,而且在兩個排行榜上他都是第一名。那就是湯瑪斯?曼。(在十二部長篇小說榜中,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和女兒克勞思?曼,分別位列第二名和第六名,一家子占了四分之一名額)二十世紀一百年間,德國出了多少傑出優秀的小說作家,唯有湯瑪斯?曼如此獨占鰲頭。可見他有多重要,有多偉大。
湯瑪斯?曼的重要與偉大,不僅只在小說創作上。他的思想、性格,他對國家、民族、社會、土地的情感、態度、觀點、立場,在在都成為現代德國文化無與倫比、無可替代、無人能出其右的象徵與典型。在《德意志靈魂》這本文化辭典所列舉的六十四個論述範疇裡,湯瑪斯?曼作為引據、例證,一再地出現在高達八個主題篇章之中。古往今來,幾百年間,德國出了多少卓越頂尖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以及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的創造貢獻者,歌德、席勒、康德、尼采、黑格爾、馬克思、貝多芬、普朗克、海森堡……,通通和湯瑪斯?曼沒得比,頂多現身個一、二次。可見他有多重要,有多偉大!
在德國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偉大程度,以同樣的指標判斷,唯一可以和湯瑪斯?曼並駕齊驅的就只有華格納。《德意志靈魂》分別在九個不同的文化主題列舉華格納作為引申說明,二個人遙遙領先所有的德國才智。一個是文學,一個是音樂。而華格納的音樂,其實出發於文學。湯瑪斯?曼的文學,原點和形式本來就是音樂。二者不能說互為表裡,是朝著不同面向,各自開啟、烘托、塗抹、渲染,創造了一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空間。
不無遺憾的,因著年代日遠和距離疏遙,當代台灣人對湯瑪斯?曼的理解是稀少的,訊息也是貧乏的。他的中文繁體譯作現今找得到的只有一本《魔山》,要讀中文本,頂多還有幾本簡體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即《布登勃魯克家族》)、《浮士德博士》、《海因里希殿下》和《死於威尼斯》(即《魂斷威尼斯》)。像我這種不懂德文的人,就只能閱讀英譯本的湯瑪斯?曼作品了。即便有著時空隔閡的不解和譯本賞析的困難,《凡一?一凡》這部作品向湯瑪斯?曼致敬的企圖仍是明顯強烈的。雖然明知道在小說所嘗試探討的議題上,永無法超脫湯瑪斯?曼文學曾經處理過的論域(domain)。在書寫所希望表達的內涵上,永不能觸抵湯瑪斯?曼已經到達的靈魂深度。《凡一?一凡》的致敬儀態,在不自覺之間,採用的正是湯瑪斯?曼從華格納的音樂那兒學來的敘事形式,二人創作體例上的交集:主導動機(leitmotif)。甚且將湯瑪斯?曼文學和華格納音樂,作為故事中不斷反覆,主導敘述意旨的主題。一再地在小說篇章中,出現又出現。(總計,湯瑪斯?曼在全書五個章節中被提及。華格納比他多一次,六個。)
主導動機的形式運作,在《凡一?一凡》中,不只適用於湯瑪斯?曼和華格納,其他的人物、場景、現象,也有著近似的表現手法:先有媽祖遶境的冷知識對話,後有百年媽祖會的收驚安神;總是田家美食廚房必備的各地美食豬腳,最後總結為一碗迎接孩子歷劫歸來的豬腳麵線;還有那令人不甚愉快的銅像斷頭、石碑破壞、石犬毀損,乃至終止於一副身首異處的軀體。書中可以找到以主導動機手法表現的地方還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這部作品所期待討論的「議題」吧。
在主導動機的節奏韻律中,《凡一?一凡》故事反覆叩問的核心命題是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死亡與自由;附隨伴奏的次命題則是:故鄉、父子與愛情。這樣的多重議題,透過凡一VS.一凡,一種鏡像對立的反射,層層的起音、開展、奏鳴、環繞、收束。死亡起始於無能無奈的棄世之約,再生於告別式之中生命原型群像的湧現;自由起自於對意義與價值的質疑,而必須在夢境與現實中去找尋並發現如何認識自己;故鄉從自願與被迫的放逐開始,體現到不完美的本然性格之後,才有了歸屬和接納;父子在逃脫或離別的境遇之中,東尼奧、湯瑪斯?曼、波西瓦,以及一凡和獄中的爸爸,這許多對的父與子,各自有著不同的情節與連結;至於愛情,即便是個虛無的漂浪者,也能夠經由馴服找到永恆,那是一凡的青春、凡一的等待,以及唐懷瑟的救贖。主導動機格律中的鏡像或對立,不只是凡一VS.一凡、父VS.子、華格納VS.湯瑪斯?曼,也是死亡VS.生命、自由VS.愛、故鄉VS.旅人(犯人)、日本VS.台灣。在對立映照之間,故事血肉題材的演奏描繪,有些是伏筆和揭曉,有些則是隱喻及象徵。那是德意志的精神、不列顛的傳奇,那是音樂與詩,終結在最後的告別式場:音樂,是德意志的安魂曲;詩,是不列顛詩人的祈禱詞。總歸一切,這所有的對映,所有的主導與主題,都是為著訴說現實與夢境、光明與黑暗,都是為著召喚超越與認識自己,為著找尋神與我的所在。
《凡一?一凡》相較於作者之前的《少年凡一》,是一種反向的「無邊際書寫」。《少年凡一》是在虛構的日本時空場景中填充界線難辨的真實;《凡一?一凡》則是在真實的台灣時空舞台裡添飾醒寐不清的虛構。這是作者用以說服自己面對真實的方式,在個人的夢境,如兩位台日青年;或集體的神話,如德意志、不列顛乃至台灣這個國家,都指向一種英雄自我追尋歷程的呈現。這樣子以自己人生實上加虛的書寫形式,在真誠面對的同時,是否也有著過度揭露的問題?英國當代最重要的女性小說家也是評論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她影響世人至深的名作《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裡曾經這麼說:
小說像是一面蜘蛛網,它的尖角黏附於人生上面。……這些網不是那些視之無形的小蟲在空中織成的,而是一些受著痛苦的煎熬的人的作品。
所以,小說與實際的人生一致,其價值也是在某一程度內與實際的生活相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定得照清自己的靈魂,它的深奧處,它的膚淺處,它的虛榮,它的慷慨,還要自己說出你面貌的美麗或平凡。
吳爾芙的觀點,令我不致擔心《凡一?一凡》在真實性上的過與不及。應該憂慮的是,作品能不能達到吳爾芙對於小說的要求--
小說(應該)觸引起我們各種相反的、相矛盾的情感。
就小說家而言,所謂的誠實,就是他能給予一個信念:相信「此即真」。
真是太難了!尤其是像《凡一?一凡》這樣,在寫實之上堆疊累加虛擬,虛擬好瞎掰,寫實難處理。究竟,寫實主義是如何營造的?有沒有一個「現實原則」,讓我們依偏好去拿捏掌握現實重現的恰當程度。劉森堯教授在他的《讀書》這部評論集中,比較了三位歷史上重要偉大的寫實主義文學家:
狄更斯:是社會現象的見證者,服膺的「現實原則」是寫出他眼中所看到的真實面。
福樓拜:他的寫實主義不在「現實的重現」,反而是個人「現實的重造」。
湯瑪斯.曼:不批判,只有反省,並臣服於命運的法則、衰落和死亡。他眼中的人生真諦,才是小說中的「現實原則」。
透過以上解析,三大文豪的境界異同高下立判。事實上,湯瑪斯.曼的寫實早已超越了寫實,在寫實之中添加了大量的魔幻虛擬元素。就如同劉教授所指出的,「虛構」最能冷靜反映真正的現實面。是以我不太在乎《凡一?一凡》故事在虛實之間擺盪的幅度,比較在意的反而是人物所能夠帶出的意義。比如,一凡有一位專門(也只能)務虛談論真理的父親,和一個除了張羅準備豬腳、綠豆椪、道地小吃,還能講解校園民歌、外省文學、台語歌曲,以及民主化發展,相對之下極為務實的母親。立虹這個角色,特別值得在此一提。因為故鄉永遠需要一位母親。
她的胸懷,是包含廣納、兼容並蓄的;
她的思想、歷史感、文明觀,是具備縱深且恢弘寬闊的;
她的性格、良知、信念,是充滿著正面提昇能量的;
她的視野、觀點,是洞察透徹而又跨越領域的。
若沒有一位這樣的母親,台灣文明地層的堆疊累加,不但將難以形成意義,甚至只能支離破碎。我暗自期許,《凡一?一凡》中的立虹,作為台灣新時代母親的典範原型,在現實世界中,一定還有很多、很多……。
雖然米蘭?昆德拉這麼主張:
小說不能肯定任何事物;小說永遠在尋找和提出疑問。我不知道我的國家會不會毀滅,我也不知道我筆下的人物對不對。我編造故事,讓故事衝突對抗,從中提出疑問。
我還是一個愛好自問必自答的死硬派。《凡一?一凡》書中提出的集體性問題,諸如:大學教育的任務、原住民身分的自我認同與型塑、拼布化破碎台灣的現況與展望;以及個體性的困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活著做什麼、我到底是誰。好比來自德、英的夢境喻意,啟示就刻劃在希臘的神殿上面一般。每一項課題,我都希望儘可能地即使沒有完美的答案,至少也試著解釋或指出方向,作出力所能及的完結處理。因為,總是要求自己的作品,要像一個可以整除、餘數為零的除法算式一樣,才比較負責任。《凡一?一凡》故事裡,唯一有意識地沒留下答案的,是結尾無頭軀體的處決者。這一情節本來是當成答案的,沒想到竟成了破洞很大的謎題。對於因此而不滿怪罪我不負責任的讀者,我只能懇求恕罪了。
作品的意圖解說得再多,故事本身不好看,小說的價值就天搖地動了。《凡一?一凡》好不好看,只能留待讀者們評鑑。不過如果有人告訴你,湯瑪斯.曼的小說好好看,那絕對是忽攏你的。相信我,這位德國最重要偉大文豪的作品,每一部都不好看極了。文學之於湯瑪斯?曼就是某種「迴聲」,用他自己的話語來說:
這種迴聲,這種把人的聲音作為自然的聲音的歸還,……從本質上講就是哀歌,……就是自然試圖宣告:人是孤獨的。
孤獨迴聲的哀歌文學,把它寫出來還諸自然。對以此為天職的小說家來說,好不好看,就可以不重要了。
即便自我再怎麼孤獨,也還是能夠滿懷情感的包容這個時代、這個世界。仰望這樣的湯瑪斯?曼,我只能羨慕、佩服加上崇敬。
在命運的安排下,互相激盪,追尋生命的意義。
「對於生命無感而可能只好自我了結的凡一,自己的價值在哪裡?」他是凡一。
「感情關係上呈現無政府主義的一凡,或許在內心精神上是一種虛無主義吧。」這是一凡。
一場又一場的夢境,會把青年帶向何處,
透過夢的解析,可以得到「我是誰」、「如何得到快樂」、「生命的意義何在」嗎?
以及,人生終極的目標是什麼呢,必須透過湯瑪斯?曼的小說,華格納的音樂,聖杯傳奇與希臘哲人,來關照生命的真相。
自由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如何塑造台灣的命運共同體?
這是台灣人共同的使命嗎?
台灣的美食聞名全球,媽祖遶境刻劃土地情深,泰雅的祖靈在召喚,斷頭的石碑是奉獻者的精神,
這些都是銘刻台灣文化的內涵事件,是一場無盡的饗宴,還是魅影縈繞糾纏?
繼《少年凡一》、《彩虹麗子》後,藤原進三的第三部小說。主角凡一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就讀,卻無法融入校園生活,課業糟糕,不能跟上學校的步調,經常有挫敗厭世之感。一次到台灣旅行,剛好遇到心儀的教授在台灣做選情觀察研究,在教授的要求下完成測試並決定到台大當交換學生。接待他的台北寄宿家庭中,剛好有跟他同年齡的台大法律系學生一凡,兩人同一個屋簷下,展開探索台灣、追問生命意義的旅程。期間,凡一與一凡經常為夢中的景象所困擾,經由一凡母親立虹的牽引,將困擾的夢中情景寫給不在家的父親,每每都能得到一凡的啟發,了解生命的意義。
這兩位年輕人除了為夢境所擾,在台灣的生活卻豐富多采又緊湊,週間在台大求學,交朋友,每個週末都會有立虹為他們準備的早午餐,來自台灣各地的豬腳、糕餅、麵線各式美食,一凡維持每個週末到武塔當課輔小老師,凡一跟進,他們在此與到完全不同類型的人,生活方式,瞭解到台灣原住民歷史與困境。
這部小說卻不止於圍繞著這兩位年輕人,作者創造了另一條貼近社會時事的故事,也是追查台日情節的線索,翻開台灣日本時代、國民黨政權帶來的移民,所交織的族群問題。
這是一本恢弘博雅的成長小說有凡一與一凡、父與子、華格納與湯瑪斯.曼,也有死亡VS.生命、自由VS.愛、故鄉VS.旅人(犯人)、日本VS.台灣。鏡像對立映照,故事血肉題材的演奏描繪,有些是伏筆和揭曉,有些則是隱喻及象徵。
〈自序〉
在主導動機的樂聲話語中拷問靈魂
我寧願什麼也不說,也不願說得微弱。
--米勒(Jean Michelet)
這是一個父親寫給孩子的故事。橫亙在父與子的關係之間,進行著生命的凝視,聳立在前的是世代相對的巨大歧異。依稀記得我這一代人,年輕的時候,似乎多數是再怎麼樣也要拚下去的不惜掙扎;可看著、聽著當前的年輕世代,茫然中又具體明晰地漫佈著一股寧可棄世也不願低頭的倔強,這種氛圍態度,令我驚慌到甚至戰慄不已。
我們到底造就出了什麼樣的生存環境,讓年輕人將厭世當做一種選擇?這迫使年少心性趨向離世的生命困局、世間處境,是怎麼構陷出來的?
死亡,做為一個命運或抉擇的課題,終究還是得在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發現過程中,去尋求解答吧!若能找得到那即便只有希微渺弱的一點點,就像天空中垂降下來的一根蜘蛛絲,說不定還是有攀附而昇、超脫救贖的機會。不然就只能淪落幽暗了。
就算僅有一絲絲的光明、一些些的希望,還是得朝著那光明與希望的縫隙盡力而去,生命才能有超越的機會。這不應該只是我、或像我這一世代人的思維,而是跨越世代生而為人共同的信念才對吧。想對孩子說一個這樣的故事,怎麼樣在不失批判性精神的同時,能夠以一種比較具有包容性的立場與觀點,去觀照省思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這塊土地、這群人們。這堂而皇之的嚴肅主題,甫一觸及,立即在我腦中浮現的表現形式與意義典範,就是湯瑪斯?曼(Paul Thomas Mann)這位德意志最重要、最偉大的文學心靈創作者。
湯瑪斯?曼有多重要?有多偉大?兩位文化觀察╱理論名家苔雅?朱恩(Thea Dorn)和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最新出版的《德意志靈魂》(Die Deutsche Seele,台灣譯名:《德國文化關鍵詞:從德意志到德國的64個核心概念》),這部厚達九百頁的鉅著,以六十四個文化行為、現象、傳統、典範、創造領域,完整、豐富、深刻,而且批判地呈現、解析了德國文化的內涵、精神、本質,以及獨特性。作者在書中開列了兩份權威性無可挑戰的清單:「二十世紀十部最具實驗性的德語小說」、「二十世紀十二部最重要的德語長篇小說」,只有一位文學家同時名列雙榜,而且在兩個排行榜上他都是第一名。那就是湯瑪斯?曼。(在十二部長篇小說榜中,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和女兒克勞思?曼,分別位列第二名和第六名,一家子占了四分之一名額)二十世紀一百年間,德國出了多少傑出優秀的小說作家,唯有湯瑪斯?曼如此獨占鰲頭。可見他有多重要,有多偉大。
湯瑪斯?曼的重要與偉大,不僅只在小說創作上。他的思想、性格,他對國家、民族、社會、土地的情感、態度、觀點、立場,在在都成為現代德國文化無與倫比、無可替代、無人能出其右的象徵與典型。在《德意志靈魂》這本文化辭典所列舉的六十四個論述範疇裡,湯瑪斯?曼作為引據、例證,一再地出現在高達八個主題篇章之中。古往今來,幾百年間,德國出了多少卓越頂尖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以及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的創造貢獻者,歌德、席勒、康德、尼采、黑格爾、馬克思、貝多芬、普朗克、海森堡……,通通和湯瑪斯?曼沒得比,頂多現身個一、二次。可見他有多重要,有多偉大!
在德國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偉大程度,以同樣的指標判斷,唯一可以和湯瑪斯?曼並駕齊驅的就只有華格納。《德意志靈魂》分別在九個不同的文化主題列舉華格納作為引申說明,二個人遙遙領先所有的德國才智。一個是文學,一個是音樂。而華格納的音樂,其實出發於文學。湯瑪斯?曼的文學,原點和形式本來就是音樂。二者不能說互為表裡,是朝著不同面向,各自開啟、烘托、塗抹、渲染,創造了一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空間。
不無遺憾的,因著年代日遠和距離疏遙,當代台灣人對湯瑪斯?曼的理解是稀少的,訊息也是貧乏的。他的中文繁體譯作現今找得到的只有一本《魔山》,要讀中文本,頂多還有幾本簡體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即《布登勃魯克家族》)、《浮士德博士》、《海因里希殿下》和《死於威尼斯》(即《魂斷威尼斯》)。像我這種不懂德文的人,就只能閱讀英譯本的湯瑪斯?曼作品了。即便有著時空隔閡的不解和譯本賞析的困難,《凡一?一凡》這部作品向湯瑪斯?曼致敬的企圖仍是明顯強烈的。雖然明知道在小說所嘗試探討的議題上,永無法超脫湯瑪斯?曼文學曾經處理過的論域(domain)。在書寫所希望表達的內涵上,永不能觸抵湯瑪斯?曼已經到達的靈魂深度。《凡一?一凡》的致敬儀態,在不自覺之間,採用的正是湯瑪斯?曼從華格納的音樂那兒學來的敘事形式,二人創作體例上的交集:主導動機(leitmotif)。甚且將湯瑪斯?曼文學和華格納音樂,作為故事中不斷反覆,主導敘述意旨的主題。一再地在小說篇章中,出現又出現。(總計,湯瑪斯?曼在全書五個章節中被提及。華格納比他多一次,六個。)
主導動機的形式運作,在《凡一?一凡》中,不只適用於湯瑪斯?曼和華格納,其他的人物、場景、現象,也有著近似的表現手法:先有媽祖遶境的冷知識對話,後有百年媽祖會的收驚安神;總是田家美食廚房必備的各地美食豬腳,最後總結為一碗迎接孩子歷劫歸來的豬腳麵線;還有那令人不甚愉快的銅像斷頭、石碑破壞、石犬毀損,乃至終止於一副身首異處的軀體。書中可以找到以主導動機手法表現的地方還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這部作品所期待討論的「議題」吧。
在主導動機的節奏韻律中,《凡一?一凡》故事反覆叩問的核心命題是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死亡與自由;附隨伴奏的次命題則是:故鄉、父子與愛情。這樣的多重議題,透過凡一VS.一凡,一種鏡像對立的反射,層層的起音、開展、奏鳴、環繞、收束。死亡起始於無能無奈的棄世之約,再生於告別式之中生命原型群像的湧現;自由起自於對意義與價值的質疑,而必須在夢境與現實中去找尋並發現如何認識自己;故鄉從自願與被迫的放逐開始,體現到不完美的本然性格之後,才有了歸屬和接納;父子在逃脫或離別的境遇之中,東尼奧、湯瑪斯?曼、波西瓦,以及一凡和獄中的爸爸,這許多對的父與子,各自有著不同的情節與連結;至於愛情,即便是個虛無的漂浪者,也能夠經由馴服找到永恆,那是一凡的青春、凡一的等待,以及唐懷瑟的救贖。主導動機格律中的鏡像或對立,不只是凡一VS.一凡、父VS.子、華格納VS.湯瑪斯?曼,也是死亡VS.生命、自由VS.愛、故鄉VS.旅人(犯人)、日本VS.台灣。在對立映照之間,故事血肉題材的演奏描繪,有些是伏筆和揭曉,有些則是隱喻及象徵。那是德意志的精神、不列顛的傳奇,那是音樂與詩,終結在最後的告別式場:音樂,是德意志的安魂曲;詩,是不列顛詩人的祈禱詞。總歸一切,這所有的對映,所有的主導與主題,都是為著訴說現實與夢境、光明與黑暗,都是為著召喚超越與認識自己,為著找尋神與我的所在。
《凡一?一凡》相較於作者之前的《少年凡一》,是一種反向的「無邊際書寫」。《少年凡一》是在虛構的日本時空場景中填充界線難辨的真實;《凡一?一凡》則是在真實的台灣時空舞台裡添飾醒寐不清的虛構。這是作者用以說服自己面對真實的方式,在個人的夢境,如兩位台日青年;或集體的神話,如德意志、不列顛乃至台灣這個國家,都指向一種英雄自我追尋歷程的呈現。這樣子以自己人生實上加虛的書寫形式,在真誠面對的同時,是否也有著過度揭露的問題?英國當代最重要的女性小說家也是評論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她影響世人至深的名作《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裡曾經這麼說:
小說像是一面蜘蛛網,它的尖角黏附於人生上面。……這些網不是那些視之無形的小蟲在空中織成的,而是一些受著痛苦的煎熬的人的作品。
所以,小說與實際的人生一致,其價值也是在某一程度內與實際的生活相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定得照清自己的靈魂,它的深奧處,它的膚淺處,它的虛榮,它的慷慨,還要自己說出你面貌的美麗或平凡。
吳爾芙的觀點,令我不致擔心《凡一?一凡》在真實性上的過與不及。應該憂慮的是,作品能不能達到吳爾芙對於小說的要求--
小說(應該)觸引起我們各種相反的、相矛盾的情感。
就小說家而言,所謂的誠實,就是他能給予一個信念:相信「此即真」。
真是太難了!尤其是像《凡一?一凡》這樣,在寫實之上堆疊累加虛擬,虛擬好瞎掰,寫實難處理。究竟,寫實主義是如何營造的?有沒有一個「現實原則」,讓我們依偏好去拿捏掌握現實重現的恰當程度。劉森堯教授在他的《讀書》這部評論集中,比較了三位歷史上重要偉大的寫實主義文學家:
狄更斯:是社會現象的見證者,服膺的「現實原則」是寫出他眼中所看到的真實面。
福樓拜:他的寫實主義不在「現實的重現」,反而是個人「現實的重造」。
湯瑪斯.曼:不批判,只有反省,並臣服於命運的法則、衰落和死亡。他眼中的人生真諦,才是小說中的「現實原則」。
透過以上解析,三大文豪的境界異同高下立判。事實上,湯瑪斯.曼的寫實早已超越了寫實,在寫實之中添加了大量的魔幻虛擬元素。就如同劉教授所指出的,「虛構」最能冷靜反映真正的現實面。是以我不太在乎《凡一?一凡》故事在虛實之間擺盪的幅度,比較在意的反而是人物所能夠帶出的意義。比如,一凡有一位專門(也只能)務虛談論真理的父親,和一個除了張羅準備豬腳、綠豆椪、道地小吃,還能講解校園民歌、外省文學、台語歌曲,以及民主化發展,相對之下極為務實的母親。立虹這個角色,特別值得在此一提。因為故鄉永遠需要一位母親。
她的胸懷,是包含廣納、兼容並蓄的;
她的思想、歷史感、文明觀,是具備縱深且恢弘寬闊的;
她的性格、良知、信念,是充滿著正面提昇能量的;
她的視野、觀點,是洞察透徹而又跨越領域的。
若沒有一位這樣的母親,台灣文明地層的堆疊累加,不但將難以形成意義,甚至只能支離破碎。我暗自期許,《凡一?一凡》中的立虹,作為台灣新時代母親的典範原型,在現實世界中,一定還有很多、很多……。
雖然米蘭?昆德拉這麼主張:
小說不能肯定任何事物;小說永遠在尋找和提出疑問。我不知道我的國家會不會毀滅,我也不知道我筆下的人物對不對。我編造故事,讓故事衝突對抗,從中提出疑問。
我還是一個愛好自問必自答的死硬派。《凡一?一凡》書中提出的集體性問題,諸如:大學教育的任務、原住民身分的自我認同與型塑、拼布化破碎台灣的現況與展望;以及個體性的困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活著做什麼、我到底是誰。好比來自德、英的夢境喻意,啟示就刻劃在希臘的神殿上面一般。每一項課題,我都希望儘可能地即使沒有完美的答案,至少也試著解釋或指出方向,作出力所能及的完結處理。因為,總是要求自己的作品,要像一個可以整除、餘數為零的除法算式一樣,才比較負責任。《凡一?一凡》故事裡,唯一有意識地沒留下答案的,是結尾無頭軀體的處決者。這一情節本來是當成答案的,沒想到竟成了破洞很大的謎題。對於因此而不滿怪罪我不負責任的讀者,我只能懇求恕罪了。
作品的意圖解說得再多,故事本身不好看,小說的價值就天搖地動了。《凡一?一凡》好不好看,只能留待讀者們評鑑。不過如果有人告訴你,湯瑪斯.曼的小說好好看,那絕對是忽攏你的。相信我,這位德國最重要偉大文豪的作品,每一部都不好看極了。文學之於湯瑪斯?曼就是某種「迴聲」,用他自己的話語來說:
這種迴聲,這種把人的聲音作為自然的聲音的歸還,……從本質上講就是哀歌,……就是自然試圖宣告:人是孤獨的。
孤獨迴聲的哀歌文學,把它寫出來還諸自然。對以此為天職的小說家來說,好不好看,就可以不重要了。
即便自我再怎麼孤獨,也還是能夠滿懷情感的包容這個時代、這個世界。仰望這樣的湯瑪斯?曼,我只能羨慕、佩服加上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