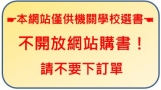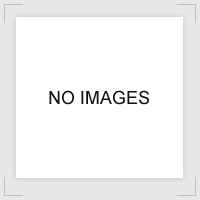這個世界只在乎你
是否在到達了一定的高度,
而不在乎你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去的,
還是踩在垃圾上上去的。
人活在世上,要讓人瞧得起。所以,在世俗生活中,人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己和他人之間進行測量,心照不宣地交換著彼此的眼神。
人活在世上,要讓人瞧得起。這是天下有心父母對孩子的諄諄教導。為了讓別人瞧得上眼,看得順眼,就必須往身上披東西往腳底墊東西,使自己高大而風光。
在一個權力財富打不爛、分不平的天下,尊嚴是一種不可抑制的人生要求,特別是當這種不平是可以通過個人奮鬥打破的時候,仰人鼻息便是無能的標誌。每個人都像發情的駝鳥拉長脖子以高人一等,誰都爭當峰頭的小草,不願做谷底的青松。
這種世俗的水準攀比對人的煎熬,甚至超過生命的原欲。那些一出生就寓人籬下的可憐孩子們,在夜半三更人們睡深夢酣時,還在咬牙切齒暗下決心。那些有著自我擴張意念的人,時刻準備像烈馬一樣奮蹄從千萬人的眼睛上踐踏而過。
尊嚴的要求一部分是出自擺脫別人的意志或支配別人意志,一部分則是為了在眾人眼前顯耀一種焰火爆竹的輝煌。女人企圖把異性的垂涎和同性的嫉妒集於一身,男人則要讓天下男人黯然失色,讓所有女人因為與他無緣而遺恨千古。
總之,尊嚴的追求回盪著英雄主義的旋律,只不過這個英雄只管征服不管拯救,他實際上只為了在金字塔上拾個高臺階擺個好造型。這種尊嚴就是所謂「體面」,它表明我們生活在他人炯炯目光之下,並千方百計取媚和征服這種目光。
在世俗生活中,人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己和他人之間進行測量,心照不宣地交換著彼此的眼神。正像小城鎮上的暴發戶相互較量樓層的高低和節日鞭炮的長短一般,為了贏得他人的豔羨和驚訝,我們不斷模擬他人的景仰來調整自己的行為,改變自己的生活。我們把自己的服裝和髮式改換得讓別人看起來「好看」,我們把起居環境佈置得讓別人看起來「優雅」,我們檢點自己的行為舉止,讓別人看起來「高貴」,卻常常忘了捫心自問自己是否適意。似乎這些服裝、髮式、廳室包括自己的行為都是為別人的生活準備的,自己不過是個僕人而已。
總之,我們在還不知道能否贏得別人之前,就已實實在在地以別人來奴役自己,像蒼蠅一樣投入他人目光的蛛網中。原來企圖征服他人眼睛的英雄,反倒成了他人目光的俘虜,被他人的視線束縛和牽引,要從他人的眼色中來尋找人生的價值和方向。越多的他人看得熱眼就說明你重要,而當他人以冷漠不屑鄙夷的眼神注視你或是轉眼不看你時,你就一文不值,失落下來而不知如何是好。人前的風光常常與身後的蕭條相映成趣。
當社會的水準梯度力超過生命本身原欲時,尊嚴體面的追求便使我們為他人的目光所奴役,無法按自己的本性自由輕鬆地呼吸。然而,尊嚴是什麼東西?體面是什麼玩藝?
尊嚴只是相對別人的威懾和侵犯而產生的,相對於自己便無所謂尊嚴了。如果地球上人人平等友好或只有你一個人,尊嚴算什麼東西!
體面是相對於別人不善的目光來說的,它表明我們畏懼他人的目光,把自己的眼睛長到了他人的腦袋上。如果世上所有的人都失明,只剩下你一雙眼睛,你全身披掛花環、勳章、珠寶項鏈豈不荒唐!
自尊心的強烈只能證明我們過於在乎別人的存在,體面的過度講究只能說明我們蔑視自己的性命,對內心的呼喚置若罔聞,而諂媚於他人的現眼。
每個不免於俗的人都不可避免要投入他人目光的羅網中去。然而,我能否活得自由,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能否把自己從睽睽眾目中解脫出來,撥開刀光劍影般的眼神,進入無人之境,發現自己生命歡悅的所在,按照自己的情趣和天真本性活活脫脫地生活,在澄明的境界中開盡生活的繁花。
在他人目光失明的地方,是你真正生活的開始。
是否在到達了一定的高度,
而不在乎你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去的,
還是踩在垃圾上上去的。
人活在世上,要讓人瞧得起。所以,在世俗生活中,人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己和他人之間進行測量,心照不宣地交換著彼此的眼神。
人活在世上,要讓人瞧得起。這是天下有心父母對孩子的諄諄教導。為了讓別人瞧得上眼,看得順眼,就必須往身上披東西往腳底墊東西,使自己高大而風光。
在一個權力財富打不爛、分不平的天下,尊嚴是一種不可抑制的人生要求,特別是當這種不平是可以通過個人奮鬥打破的時候,仰人鼻息便是無能的標誌。每個人都像發情的駝鳥拉長脖子以高人一等,誰都爭當峰頭的小草,不願做谷底的青松。
這種世俗的水準攀比對人的煎熬,甚至超過生命的原欲。那些一出生就寓人籬下的可憐孩子們,在夜半三更人們睡深夢酣時,還在咬牙切齒暗下決心。那些有著自我擴張意念的人,時刻準備像烈馬一樣奮蹄從千萬人的眼睛上踐踏而過。
尊嚴的要求一部分是出自擺脫別人的意志或支配別人意志,一部分則是為了在眾人眼前顯耀一種焰火爆竹的輝煌。女人企圖把異性的垂涎和同性的嫉妒集於一身,男人則要讓天下男人黯然失色,讓所有女人因為與他無緣而遺恨千古。
總之,尊嚴的追求回盪著英雄主義的旋律,只不過這個英雄只管征服不管拯救,他實際上只為了在金字塔上拾個高臺階擺個好造型。這種尊嚴就是所謂「體面」,它表明我們生活在他人炯炯目光之下,並千方百計取媚和征服這種目光。
在世俗生活中,人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己和他人之間進行測量,心照不宣地交換著彼此的眼神。正像小城鎮上的暴發戶相互較量樓層的高低和節日鞭炮的長短一般,為了贏得他人的豔羨和驚訝,我們不斷模擬他人的景仰來調整自己的行為,改變自己的生活。我們把自己的服裝和髮式改換得讓別人看起來「好看」,我們把起居環境佈置得讓別人看起來「優雅」,我們檢點自己的行為舉止,讓別人看起來「高貴」,卻常常忘了捫心自問自己是否適意。似乎這些服裝、髮式、廳室包括自己的行為都是為別人的生活準備的,自己不過是個僕人而已。
總之,我們在還不知道能否贏得別人之前,就已實實在在地以別人來奴役自己,像蒼蠅一樣投入他人目光的蛛網中。原來企圖征服他人眼睛的英雄,反倒成了他人目光的俘虜,被他人的視線束縛和牽引,要從他人的眼色中來尋找人生的價值和方向。越多的他人看得熱眼就說明你重要,而當他人以冷漠不屑鄙夷的眼神注視你或是轉眼不看你時,你就一文不值,失落下來而不知如何是好。人前的風光常常與身後的蕭條相映成趣。
當社會的水準梯度力超過生命本身原欲時,尊嚴體面的追求便使我們為他人的目光所奴役,無法按自己的本性自由輕鬆地呼吸。然而,尊嚴是什麼東西?體面是什麼玩藝?
尊嚴只是相對別人的威懾和侵犯而產生的,相對於自己便無所謂尊嚴了。如果地球上人人平等友好或只有你一個人,尊嚴算什麼東西!
體面是相對於別人不善的目光來說的,它表明我們畏懼他人的目光,把自己的眼睛長到了他人的腦袋上。如果世上所有的人都失明,只剩下你一雙眼睛,你全身披掛花環、勳章、珠寶項鏈豈不荒唐!
自尊心的強烈只能證明我們過於在乎別人的存在,體面的過度講究只能說明我們蔑視自己的性命,對內心的呼喚置若罔聞,而諂媚於他人的現眼。
每個不免於俗的人都不可避免要投入他人目光的羅網中去。然而,我能否活得自由,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能否把自己從睽睽眾目中解脫出來,撥開刀光劍影般的眼神,進入無人之境,發現自己生命歡悅的所在,按照自己的情趣和天真本性活活脫脫地生活,在澄明的境界中開盡生活的繁花。
在他人目光失明的地方,是你真正生活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