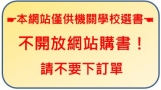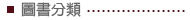【本書簡介】
◎代理經銷 白象文化
【作者簡介】
◎阮平方(Nguyễn Bình Phương)本名阮文平( Nguyễn Văn Bình)1965年出生於越南太原市,1985年從軍;曾在越南北部邊境地區工作。目前擔任越南作家協會副主席、越南軍隊文藝雜誌總編輯。自1990年起開始創作,其作品文類涵蓋詩與散文。已出版10部小說與6本詩集,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文、法文、日文、中文、瑞典文及韓文等多國語言, 廣受國際讀者的喜愛與認可。
【推薦序】
◎
關於本書
2012
首次在美國發行,
書名為《車上坡、車下坡》(Xe lên xe xuống),
由世紀論壇出版社(NXB Diễn đàn thế kỷ)出版。
2014
在越南正式發行,書名為《Mình và họ》,
由年輕出版社(NXB Trẻ)出版,
至 2024 年止已經再版4 次。
2023
翻譯成韓文於韓國出版。
2025
由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策畫,
翻譯成繁體中文版在台灣出版。
2015
榮獲河內作家協會文學獎
2020
榮獲越南作家協會
「保護邊界、海島題材」首獎
【作者序】
◎
我寫《我們與他們》是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構思。這部小說的命運最初相當坎坷,因為多家國內出版社拒絕出版,原因是該作品涉及的問題--越南與中國的邊界衝突。然而,當這本書最終得以出版並且獲得兩個獎項後,它逐漸獲得了更好的迴響。
事實上,《我們與他們》有兩個層面,一方面是講述越南人民在北部邊境保衛戰中與中國侵略者的激烈戰鬥。這可以說是一場悲壯且慘烈的戰爭,對越南人來說,這樣的經歷不可能輕易地遺忘。另一方面,我也探討了某些人在面對與社會共同體的關係時所表現出的迷茫和困惑。這些人在生活中經常面臨暴力的牢籠所箝制,這使得他們感到困惑,甚至是迷失。我認為,一般人類至今從未擺脫過暴力,因為暴力本身正是所有暴力的根源。
小說中主角的哥哥深受與中國軍隊作戰時的血腥場面所困擾,並且不幸死於這種陰影。至於主角,他作為敘述者,則因為和平時期的暴力而死亡。然而,在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的靈魂依然對與周圍人的關係充滿痛苦,對於那些曾經努力去區分「我們的國家」與「他們的國家」的人也充滿不滿,具體而言,是越南與中國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的意圖是徹底地疏離一個不斷帶來焦慮和陰影的力量。
我無法確定這種區分究竟是該擔憂還是該高興。我也無法確定當我發現每個民族,就像每個人一樣,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民族」與「他們的民族」進行高低區分時,這是值得擔憂還是值得慶幸。但我相信這一點:在這樣的問題和比較之中,潛藏著無數的風險。當一部文學作品提出問題時,並不一定需要立刻給出答案。答案可能存在於其他作品中,甚至永遠不會有答案。作家通常只有在懷疑的時候才是對的,而當他確定時,一切都可能變得極為危險。我總是偏向那些模糊的世界,因為它們的意涵是無窮無盡的。
當得知《我們與他們》被翻譯並在台灣出版時,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樣就能讓更多越南以外的讀者接觸到這部作品。
感謝亞細亞國際傳播社善意地將《我們與他們》介紹給台灣讀者。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得到台灣讀者的共鳴與好評。
阮平方(Nguyễn Bình Phương)
2025 年 2 月 越南河內
【目錄】
◎
關於本書
作者序
本文
【內容試讀】
◎
楔子:我們、他們,糾葛於有形無形的越中邊境戰爭
殘破不堪的心靈,豈能依託在飄渺虛無的「塔文」?
車子謹慎緩慢下坡。太陽沿山脊慢慢沉下。那些臉色冷峻的人開始放慢呼吸的節奏。阿莊眨眼的動作也變得遲滯。在我突如其來的完美縱身一躍之後,一切都緩慢了下來。當時我並沒有預料到那會是穿越許多樹梢和岩石的跳躍。我也沒想到最終一切會如此輕鬆。當時我只是認為哥哥一時疏忽大意,沒有果斷地作出決定,才會被他們抓住。我不想重蹈哥哥的覆轍,也不想重犯媽媽的錯誤。
「千 萬 不 要 被 抓 到!」
哥哥加重力道、重複描粗,寫下這句話。
就在不久前,我還站在靠近界標的地方,想像哥哥是怎麼回來的……
也許哥哥背著連長從左邊繞過,那裡有兩塊台階般的大岩石,也有可能沿著斜對面的那條小徑走了上去。但是無論走哪條路回去,哥哥都不知道他們早已埋伏在那裡。我邊想邊感到毛骨悚然,不清楚是因為想像還是其他原因。他眉頭緊皺,彎腰撿起沾滿褲管的野草,嘴裡仍叼著一根菸,煙霧緩緩地往上飄。視線追隨著那縷煙霧,我注意到頭頂上方有一團奇異的雲。是五彩的雲,散發耀眼的光芒,就像一個倒扣的魚簍。我知道無法拍下這團雲,因為太陽就在它的後方。那是我在這次整個旅程中見過最寂寞的雲。雖然我手中的相機裡面裝滿了各種雲,但此刻它變成無用之物。我本來打算告訴阿莊,但看到她正在專心聽著團委書記講話,便作罷了。令我感到不安的是,那團雲幾乎沒有飄動,一直停留在那裡。我感覺有些焦躁,可能因為高海拔的關係。司機來回踱步,偶爾往輪胎上踢一腳來檢查檢查。
與縣級團委書記之前說的不同,並沒有兩側分野的現象。在界標的兩側,樹木仍是直立的生長,沒有顯露裡面的任何跡象。我彷彿站在一面大鏡子前,無法分辨這邊與那邊。
「有車子上來呢!」 豎起耳朵聽完後,司機大聲地說。
他說:「昨晚聽說林務局代表團要來,應該是他們的車。」
司機凝視下方等待,眼睛瞇著。那段道路蜿蜒曲折、隱蔽,偶爾才會露出一小段地方。
「那裡。」 司機的手指向斜坡下方,可是我沒看到,只聽到引擎的轟隆聲。縣級團委書記把阿莊拉到懸崖邊緣,手舞足蹈地說著什麼。
「不是林務局的車。」 司機說,眉頭稍愁蹙。
車子出現了,緩慢而艱難地在鋪滿石頭的地面行駛。雲團開始下沉,我是這麼覺得的。
「外省車。難怪技術這麼差。」 他伸懶腰打著哈欠說。
那是一輛黑色的七人座車。只能隱約看到司機的身影,不清楚車裡坐著多少人。
「哪裡來的車子呢?」 阿莊不知何時回來了,扯著我的袖子問。我搖頭。
「可能又是像我們一樣的愛國人士。」 他回答,呵呵笑著,四處張望後,選了一塊石頭坐下。車子慢吞吞地喀喀駛了過來。我不清楚是哪個省份的車牌,只知道是輛民用車。隨後,三個人幾乎同時走下車。他們步伐堅定、毫不猶豫地走過來,面色陰沉、冷漠。
縣級團委書記急忙上前,熱情地問:「請問各位是從哪裡來的團呢?」 沒人回答,而是往三個方向分散開來。阿莊臉色蒼白環顧四周。他預感有些異常,便猛地站了起來。
「妳叫阿莊,對嗎?」 他們之中個子高大的人邊問邊靠近。
我恍然大悟。阿莊還沒來得及反應,那個人已抓緊了她的手,雙方互相拉扯。縣級團委書記慌亂地嗯嗯啊啊後退,摔了個四腳朝天。他結結巴巴地問:「你們要幹嘛呢?」
司機默默地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當作武器,但他們之中個子最矮小的人壓低聲音說:「公安。」
閃亮的槍管指向天空,那刺眼的黑色光芒,華麗奪目。
個子高大的人尷尬地瞥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他,然後瞥了一眼司機,隨後果斷走向他,語氣堅定地問:
「你是不是阿孝?」
他愣住,搖搖頭。我看到手銬在個子高大的人手上搖擺,心裡想著:「算他們厲害。」然後我拔腿就跑。
「站住!」 背後響起雷聲般的咆哮聲。
我奮力跨了五、六步,記不清了,看到腳下的樹梢,樹梢向下斜著伸展。
「站住!不然我就開槍!」
我閉上眼睛縱身跳了下去。
伴隨著我的嗡嗡風聲中有個扭曲的聲音:「站住!站住!」
聽起來非常傲慢、張狂。然後那個張狂的聲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阿莊或是阿恒不太清晰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
「不要啊!阿孝!」
無邊無際的樹葉和樹枝唰唰作響,一開始還蠻硬的,然後變得柔軟,接著,我已無法確切地描述出與那個深淵有關的任何事物了。
光線將我托起,那種純白、輕盈、飄渺的光,消除了所有的羞愧,過了好一會我才意識到,光和我,已經融為一體。
此時我仍坐在阿莊的身旁,相同的行程,相同的座位,即使是另一輛車也無所謂。車子只是車子而已。他向我炫耀他剛申請到的那輛Land Cruiser時,我就這麼想了。
在山區,人們喜歡Land Cruiser,是因為這種車底盤高、馬力強。司機補充說,車子是省委書記用過的,才開了一萬多公里,車況良好。
「報社以前用什麼車?」 我問。
他聳聳肩,撇著嘴說:「Lada牌的舊車,引擎像老太太一樣老舊。每次出差都讓人心驚膽跳。」
這果然是好車,輕鬆上坡,大坑小坑都是小意思,絲毫不費力地越過,每次過彎只會讓人感覺輕微上下跳動,並不像其他車子那樣猛烈顛簸。那輛Lada牌的車子最後則退回給省人民委員會辦公室,讓他們分配給其他較小的單位。對我而言,什麼車都一樣,只要不熄火或剎車失靈就好。車子終究只是車子。
這個山區道路兩旁的樹木也很不一樣,樹幹裹著一層亮亮的地衣,樹枝扭曲、歪七扭八,樹根卻很正常,整齊又修長,不像其他地區的樹木那樣任性地凸起來。它們從岩石中冒出,樹根被緊緊地束縛著,因此樹木所有的生命力和靈氣都集中在樹木的上方。我想知道這片土地的樹木裡面到底是什麼。當我把這個想法大聲說出來時,不僅他,連司機也驚訝地轉頭看我。我不經意瞄了阿莊一眼。她裝作沒有聽見,眼睛直視前方,但臉上卻微微泛紅。
「裡面是一頭牛。」
他說完就嘎嘎大笑起來。司機清了清嗓子,嚴肅地說:
「也許到了塔文就能知道了。」
希望如此。
當我做完愛之後仍直直盯著阿莊的那個時,她也問過我:
「你在看什麼?」
我老實地回答:「看看裡面有什麼。」
阿莊挑眉:「真的嗎?」
「嗯,真的。」 我確認,聲音有些沙啞。阿莊站了起來,赤身裸體在我面前旋轉,導致床墊劇烈晃動。
「看吧!」 於是阿莊蹲著,挑釁地張開雙腿。我的門打開了,裡面是整個混沌而荒蕪的原始世界。
「看到誰了嗎?」 阿莊輕蔑地問、挑眉。
我用小拇指摩擦她的胸部。那天是星期四。兩天後,星期六,我看見了大海。
透過車窗向外看去,山脈與大海一樣,起起伏伏,波光粼粼,只不過那份浩瀚在遙遠的某處。
我記得那個星期六,我邀請阿莊去廣寧玩,看看大海,但她不去。我打電話給雲璃,兩人乘坐長途客運,到達廣寧時正好中午,租了一間房,躺著休息。雲璃想做愛,可是我累了。下午租了一艘船到處繞。半夜我跟雲璃做了一次愛,然後睡死過去,一覺到天亮。我沿著海灘漫步,欣賞年輕女孩。那天海灘上的女孩們都比阿莊和雲璃漂亮。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了。
雲璃說:「你是個混蛋。」
我反駁:「混蛋不會把真實想法說出來。」
雲璃環顧四周,看到沒有人注意才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下體:「總有一天我會把你的那個剪掉。」
我嘴角上揚。這件事絕不會發生,因為雲璃是世界上最愛那個的女孩。雲璃突然問:「阿莊知道我們一起出來玩嗎?」
我聳聳肩:「不清楚。知道又怎麼樣?」
「我不想讓她知道。」
我說:「那阿莊就不會知道。」
雲璃看起來不相信。似乎連我自己也不相信。阿莊總是知道該知道的一切,這幾乎是一種特殊才能,而且不僅僅是特殊才能,還是她的一個謎團。感覺她能看穿一切。當雲璃眼睛盯著陳列銀飾的櫥窗時,我喊賣報紙的女孩過來買了一份 《人民公安報》。那天是星期六,報紙內容單調乏味,幾篇愛情故事,幾則卑鄙偷窺他人私生活的低俗報導。只有一則關於嬰兒被丟棄在講武湖邊的垃圾車中的新聞引起我的關注。真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把剛出生的嬰兒扔進垃圾車裡。這兩樣東西明明毫無關聯。海風呼嘯而來,報紙被風吹得鼓了起來,皺巴巴的,我生氣地把它揉成一團,扔進旁邊的垃圾桶,忽然想到那個嬰兒可能也是被人這樣扔掉的。
我們在房間裡並排躺了一個中午。我很想睡,卻無法入睡。我把手擋在眼前,因為又看到某人正站著,張開雙腿直往我臉上撒尿。雲璃在我身旁煩躁扭動著,不時用胸部磨蹭,又把大腿擱在我身上,然後無奈地起身走進洗手間。雲璃熟睡之後,我急著想大便。我脫掉短褲,蓋在雲璃的臉上,走進廁所。我全身放鬆等待。在廁所裡的時間總是比在其他地方的時間更有意義,因為感覺同一時間能做很多事情。放鬆地坐著、思考、觀察、聆聽糞便從內往外移動的過程。
一隻蟑螂偷偷摸摸地躲在門縫裡,牠的觸角擺動著探路,接著整個身子露了出來。這隻蟑螂真漂亮,全身是一種華麗、高貴的棕色。蟑螂最獨特的是永遠不用凝視。他們自信到不需要使用眼睛。那隻蟑螂跌跌撞撞地往上爬,靠近鏡子。牠的幾隻腳謹慎而敏銳地動著。突然,牠一動也不動。一隻壁虎不知道從何處急疾地爬了過來,距離蟑螂約三個手掌時停了下來。蟑螂渺無聲息,只有觸角微微擺動。壁虎則扭動著尾巴。蟑螂就像人心果的核一樣飽滿,有光澤。壁虎果然是壁虎。我放棄,我無法把壁虎形容成其他東西。在兩隻動物之間的緊張時刻,糞便開始排出,歡暢,使人陶醉。我站起來,沖水之前還好奇地看了看糞便的樣子。總之是不錯的,形狀規則,長度適中,色澤也是健康的。順哥曾說糞便是健康最準確的指標。淙淙的沖水聲使雲璃昏昏地翻了翻身,短褲從她臉上滑落。
我記得我決定馬上回河內。雲璃反對。
我說:「妳想留下就留下,我才不要。」
雲璃委屈地嘟著嘴:「我還沒回家一趟呢!」
我並沒有阻止雲璃,她如果想就回家去一趟,我則已經待夠了。這是一個無聊的城市。我差點脫口而出說,真想對這座城市撒尿。
「你是不是想回到阿莊身邊?」
恣肆無忌的話讓我火大:「妳下次還這樣講話,我會撕爛妳的嘴,聽清楚了沒?!清楚了沒?!狗東西!」
最後我還是同意留下來等雲璃回家一趟。一個多小時後,她回來了。我問:「怎麼那麼快?」
雲璃說怕我等太久。撒謊。她家不怎麼富裕,她父母是礦工,哥哥是個重度的毒蟲,見誰都伸手要錢。這就是她從未在家裡停留超過三、四個小時的原因。
「還是我們今晚留下來?我還有個朋友,好久沒見面,我們晚上去找她玩。」 雲璃事不關己似的說著。
我把手機塞進褲袋裡,說:
「我他媽的好想對這個城市撒一泡尿。」
至今我都不懂為何忍了那麼久,最後還是把那句話吐了出來。雲璃因為家鄉受到侮辱而失落垂喪著臉。我特別討厭那些以家鄉為傲的人,那些同鄉會也令我覺得噁心。我們兩人擠上了首班的長途客運。我先跳上去,雲璃隨後上來,我並沒有留意她是否上來了。老實說我希望她會錯過這班車,回家陪陪父母。畢竟家庭仍是最安穩的地方。不過她似乎找到了比我更好的位置。我只能站在擁擠的人群當中,在黏稠而刺鼻的氣味中來回摸索。車子像一頭瘋牛一樣奔跑著、搖擺著、向前衝。透過某人的腋窩,我看見樹木、房屋、人和車飛速掠過。照這樣下去,遲早都會出事。我是這麼想的。到海陽省時,車子跟同一方向行駛的摩托車發生碰撞。我聽到刺耳的剎車聲,散發著燒焦味,伴隨著乾巴巴的巨大爆炸聲。全車人都往前傾倒。我下車時,看到那輛Way alpha牌的摩托車側翻在路邊,車尾稍微被壓扁,引擎仍然發出轟隆隆的聲音,後輪仍不停地轉動。
「看那裡!」 有人大喊。
我望向遠處,看到距離車頭近十公尺處有一堆灰色的東西。雲璃拉住我的手。我一把拖著她過去看。那是一個女人,她的頭折彎在腋下、臉色蒼白、嘴唇也毫無血色。看著那種詭異的躺姿,手腳疊在一起,我猜測沒有任何一根骨頭是完整的。唯獨一綹頭髮仍顯生機,每當微風吹過,髮絲輕輕飄動,彷彿撫摸著死者的臉龐。雲璃跑到路邊嘔吐。
我和雲璃換了一輛車,下午六點回到河內。
我約順哥去餐廳,每人喝了三杯啤酒,然後點了飯菜。我只夾了幾根蔬菜,配著白飯吃。看我對最愛吃的滷肉碰都沒碰,順哥很疑惑。等他吃完飯後,我才告訴他我不吃肉,是因為下午剛剛目睹了一場交通事故。順哥愣了一下,便扯開話題說剛找到一些有關渭川地區戰爭的俄文文獻,閒下來時會翻譯給我看。我脫口而出約他去那幾個省份玩。順哥搖頭。他對邊境不感興趣。他說過很多次,如果可以的話,人類應該齊心協力把這個世界輾平,這樣一來可以減輕麻煩。
「任何邊境都是危險的,他媽的最好避開。」
牽著車子準備回去時,順哥翻開那輛Spacy摩托車的坐墊拿出一本厚厚的書遞給我,並說了那句話。
當然,我像往常一樣點了點頭。
◎代理經銷 白象文化
【作者簡介】
◎阮平方(Nguyễn Bình Phương)本名阮文平( Nguyễn Văn Bình)1965年出生於越南太原市,1985年從軍;曾在越南北部邊境地區工作。目前擔任越南作家協會副主席、越南軍隊文藝雜誌總編輯。自1990年起開始創作,其作品文類涵蓋詩與散文。已出版10部小說與6本詩集,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文、法文、日文、中文、瑞典文及韓文等多國語言, 廣受國際讀者的喜愛與認可。
【推薦序】
◎
關於本書
2012
首次在美國發行,
書名為《車上坡、車下坡》(Xe lên xe xuống),
由世紀論壇出版社(NXB Diễn đàn thế kỷ)出版。
2014
在越南正式發行,書名為《Mình và họ》,
由年輕出版社(NXB Trẻ)出版,
至 2024 年止已經再版4 次。
2023
翻譯成韓文於韓國出版。
2025
由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策畫,
翻譯成繁體中文版在台灣出版。
2015
榮獲河內作家協會文學獎
2020
榮獲越南作家協會
「保護邊界、海島題材」首獎
【作者序】
◎
我寫《我們與他們》是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構思。這部小說的命運最初相當坎坷,因為多家國內出版社拒絕出版,原因是該作品涉及的問題--越南與中國的邊界衝突。然而,當這本書最終得以出版並且獲得兩個獎項後,它逐漸獲得了更好的迴響。
事實上,《我們與他們》有兩個層面,一方面是講述越南人民在北部邊境保衛戰中與中國侵略者的激烈戰鬥。這可以說是一場悲壯且慘烈的戰爭,對越南人來說,這樣的經歷不可能輕易地遺忘。另一方面,我也探討了某些人在面對與社會共同體的關係時所表現出的迷茫和困惑。這些人在生活中經常面臨暴力的牢籠所箝制,這使得他們感到困惑,甚至是迷失。我認為,一般人類至今從未擺脫過暴力,因為暴力本身正是所有暴力的根源。
小說中主角的哥哥深受與中國軍隊作戰時的血腥場面所困擾,並且不幸死於這種陰影。至於主角,他作為敘述者,則因為和平時期的暴力而死亡。然而,在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的靈魂依然對與周圍人的關係充滿痛苦,對於那些曾經努力去區分「我們的國家」與「他們的國家」的人也充滿不滿,具體而言,是越南與中國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的意圖是徹底地疏離一個不斷帶來焦慮和陰影的力量。
我無法確定這種區分究竟是該擔憂還是該高興。我也無法確定當我發現每個民族,就像每個人一樣,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民族」與「他們的民族」進行高低區分時,這是值得擔憂還是值得慶幸。但我相信這一點:在這樣的問題和比較之中,潛藏著無數的風險。當一部文學作品提出問題時,並不一定需要立刻給出答案。答案可能存在於其他作品中,甚至永遠不會有答案。作家通常只有在懷疑的時候才是對的,而當他確定時,一切都可能變得極為危險。我總是偏向那些模糊的世界,因為它們的意涵是無窮無盡的。
當得知《我們與他們》被翻譯並在台灣出版時,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樣就能讓更多越南以外的讀者接觸到這部作品。
感謝亞細亞國際傳播社善意地將《我們與他們》介紹給台灣讀者。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得到台灣讀者的共鳴與好評。
阮平方(Nguyễn Bình Phương)
2025 年 2 月 越南河內
【目錄】
◎
關於本書
作者序
本文
【內容試讀】
◎
楔子:我們、他們,糾葛於有形無形的越中邊境戰爭
殘破不堪的心靈,豈能依託在飄渺虛無的「塔文」?
車子謹慎緩慢下坡。太陽沿山脊慢慢沉下。那些臉色冷峻的人開始放慢呼吸的節奏。阿莊眨眼的動作也變得遲滯。在我突如其來的完美縱身一躍之後,一切都緩慢了下來。當時我並沒有預料到那會是穿越許多樹梢和岩石的跳躍。我也沒想到最終一切會如此輕鬆。當時我只是認為哥哥一時疏忽大意,沒有果斷地作出決定,才會被他們抓住。我不想重蹈哥哥的覆轍,也不想重犯媽媽的錯誤。
「千 萬 不 要 被 抓 到!」
哥哥加重力道、重複描粗,寫下這句話。
就在不久前,我還站在靠近界標的地方,想像哥哥是怎麼回來的……
也許哥哥背著連長從左邊繞過,那裡有兩塊台階般的大岩石,也有可能沿著斜對面的那條小徑走了上去。但是無論走哪條路回去,哥哥都不知道他們早已埋伏在那裡。我邊想邊感到毛骨悚然,不清楚是因為想像還是其他原因。他眉頭緊皺,彎腰撿起沾滿褲管的野草,嘴裡仍叼著一根菸,煙霧緩緩地往上飄。視線追隨著那縷煙霧,我注意到頭頂上方有一團奇異的雲。是五彩的雲,散發耀眼的光芒,就像一個倒扣的魚簍。我知道無法拍下這團雲,因為太陽就在它的後方。那是我在這次整個旅程中見過最寂寞的雲。雖然我手中的相機裡面裝滿了各種雲,但此刻它變成無用之物。我本來打算告訴阿莊,但看到她正在專心聽著團委書記講話,便作罷了。令我感到不安的是,那團雲幾乎沒有飄動,一直停留在那裡。我感覺有些焦躁,可能因為高海拔的關係。司機來回踱步,偶爾往輪胎上踢一腳來檢查檢查。
與縣級團委書記之前說的不同,並沒有兩側分野的現象。在界標的兩側,樹木仍是直立的生長,沒有顯露裡面的任何跡象。我彷彿站在一面大鏡子前,無法分辨這邊與那邊。
「有車子上來呢!」 豎起耳朵聽完後,司機大聲地說。
他說:「昨晚聽說林務局代表團要來,應該是他們的車。」
司機凝視下方等待,眼睛瞇著。那段道路蜿蜒曲折、隱蔽,偶爾才會露出一小段地方。
「那裡。」 司機的手指向斜坡下方,可是我沒看到,只聽到引擎的轟隆聲。縣級團委書記把阿莊拉到懸崖邊緣,手舞足蹈地說著什麼。
「不是林務局的車。」 司機說,眉頭稍愁蹙。
車子出現了,緩慢而艱難地在鋪滿石頭的地面行駛。雲團開始下沉,我是這麼覺得的。
「外省車。難怪技術這麼差。」 他伸懶腰打著哈欠說。
那是一輛黑色的七人座車。只能隱約看到司機的身影,不清楚車裡坐著多少人。
「哪裡來的車子呢?」 阿莊不知何時回來了,扯著我的袖子問。我搖頭。
「可能又是像我們一樣的愛國人士。」 他回答,呵呵笑著,四處張望後,選了一塊石頭坐下。車子慢吞吞地喀喀駛了過來。我不清楚是哪個省份的車牌,只知道是輛民用車。隨後,三個人幾乎同時走下車。他們步伐堅定、毫不猶豫地走過來,面色陰沉、冷漠。
縣級團委書記急忙上前,熱情地問:「請問各位是從哪裡來的團呢?」 沒人回答,而是往三個方向分散開來。阿莊臉色蒼白環顧四周。他預感有些異常,便猛地站了起來。
「妳叫阿莊,對嗎?」 他們之中個子高大的人邊問邊靠近。
我恍然大悟。阿莊還沒來得及反應,那個人已抓緊了她的手,雙方互相拉扯。縣級團委書記慌亂地嗯嗯啊啊後退,摔了個四腳朝天。他結結巴巴地問:「你們要幹嘛呢?」
司機默默地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當作武器,但他們之中個子最矮小的人壓低聲音說:「公安。」
閃亮的槍管指向天空,那刺眼的黑色光芒,華麗奪目。
個子高大的人尷尬地瞥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他,然後瞥了一眼司機,隨後果斷走向他,語氣堅定地問:
「你是不是阿孝?」
他愣住,搖搖頭。我看到手銬在個子高大的人手上搖擺,心裡想著:「算他們厲害。」然後我拔腿就跑。
「站住!」 背後響起雷聲般的咆哮聲。
我奮力跨了五、六步,記不清了,看到腳下的樹梢,樹梢向下斜著伸展。
「站住!不然我就開槍!」
我閉上眼睛縱身跳了下去。
伴隨著我的嗡嗡風聲中有個扭曲的聲音:「站住!站住!」
聽起來非常傲慢、張狂。然後那個張狂的聲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阿莊或是阿恒不太清晰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
「不要啊!阿孝!」
無邊無際的樹葉和樹枝唰唰作響,一開始還蠻硬的,然後變得柔軟,接著,我已無法確切地描述出與那個深淵有關的任何事物了。
光線將我托起,那種純白、輕盈、飄渺的光,消除了所有的羞愧,過了好一會我才意識到,光和我,已經融為一體。
此時我仍坐在阿莊的身旁,相同的行程,相同的座位,即使是另一輛車也無所謂。車子只是車子而已。他向我炫耀他剛申請到的那輛Land Cruiser時,我就這麼想了。
在山區,人們喜歡Land Cruiser,是因為這種車底盤高、馬力強。司機補充說,車子是省委書記用過的,才開了一萬多公里,車況良好。
「報社以前用什麼車?」 我問。
他聳聳肩,撇著嘴說:「Lada牌的舊車,引擎像老太太一樣老舊。每次出差都讓人心驚膽跳。」
這果然是好車,輕鬆上坡,大坑小坑都是小意思,絲毫不費力地越過,每次過彎只會讓人感覺輕微上下跳動,並不像其他車子那樣猛烈顛簸。那輛Lada牌的車子最後則退回給省人民委員會辦公室,讓他們分配給其他較小的單位。對我而言,什麼車都一樣,只要不熄火或剎車失靈就好。車子終究只是車子。
這個山區道路兩旁的樹木也很不一樣,樹幹裹著一層亮亮的地衣,樹枝扭曲、歪七扭八,樹根卻很正常,整齊又修長,不像其他地區的樹木那樣任性地凸起來。它們從岩石中冒出,樹根被緊緊地束縛著,因此樹木所有的生命力和靈氣都集中在樹木的上方。我想知道這片土地的樹木裡面到底是什麼。當我把這個想法大聲說出來時,不僅他,連司機也驚訝地轉頭看我。我不經意瞄了阿莊一眼。她裝作沒有聽見,眼睛直視前方,但臉上卻微微泛紅。
「裡面是一頭牛。」
他說完就嘎嘎大笑起來。司機清了清嗓子,嚴肅地說:
「也許到了塔文就能知道了。」
希望如此。
當我做完愛之後仍直直盯著阿莊的那個時,她也問過我:
「你在看什麼?」
我老實地回答:「看看裡面有什麼。」
阿莊挑眉:「真的嗎?」
「嗯,真的。」 我確認,聲音有些沙啞。阿莊站了起來,赤身裸體在我面前旋轉,導致床墊劇烈晃動。
「看吧!」 於是阿莊蹲著,挑釁地張開雙腿。我的門打開了,裡面是整個混沌而荒蕪的原始世界。
「看到誰了嗎?」 阿莊輕蔑地問、挑眉。
我用小拇指摩擦她的胸部。那天是星期四。兩天後,星期六,我看見了大海。
透過車窗向外看去,山脈與大海一樣,起起伏伏,波光粼粼,只不過那份浩瀚在遙遠的某處。
我記得那個星期六,我邀請阿莊去廣寧玩,看看大海,但她不去。我打電話給雲璃,兩人乘坐長途客運,到達廣寧時正好中午,租了一間房,躺著休息。雲璃想做愛,可是我累了。下午租了一艘船到處繞。半夜我跟雲璃做了一次愛,然後睡死過去,一覺到天亮。我沿著海灘漫步,欣賞年輕女孩。那天海灘上的女孩們都比阿莊和雲璃漂亮。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了。
雲璃說:「你是個混蛋。」
我反駁:「混蛋不會把真實想法說出來。」
雲璃環顧四周,看到沒有人注意才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下體:「總有一天我會把你的那個剪掉。」
我嘴角上揚。這件事絕不會發生,因為雲璃是世界上最愛那個的女孩。雲璃突然問:「阿莊知道我們一起出來玩嗎?」
我聳聳肩:「不清楚。知道又怎麼樣?」
「我不想讓她知道。」
我說:「那阿莊就不會知道。」
雲璃看起來不相信。似乎連我自己也不相信。阿莊總是知道該知道的一切,這幾乎是一種特殊才能,而且不僅僅是特殊才能,還是她的一個謎團。感覺她能看穿一切。當雲璃眼睛盯著陳列銀飾的櫥窗時,我喊賣報紙的女孩過來買了一份 《人民公安報》。那天是星期六,報紙內容單調乏味,幾篇愛情故事,幾則卑鄙偷窺他人私生活的低俗報導。只有一則關於嬰兒被丟棄在講武湖邊的垃圾車中的新聞引起我的關注。真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把剛出生的嬰兒扔進垃圾車裡。這兩樣東西明明毫無關聯。海風呼嘯而來,報紙被風吹得鼓了起來,皺巴巴的,我生氣地把它揉成一團,扔進旁邊的垃圾桶,忽然想到那個嬰兒可能也是被人這樣扔掉的。
我們在房間裡並排躺了一個中午。我很想睡,卻無法入睡。我把手擋在眼前,因為又看到某人正站著,張開雙腿直往我臉上撒尿。雲璃在我身旁煩躁扭動著,不時用胸部磨蹭,又把大腿擱在我身上,然後無奈地起身走進洗手間。雲璃熟睡之後,我急著想大便。我脫掉短褲,蓋在雲璃的臉上,走進廁所。我全身放鬆等待。在廁所裡的時間總是比在其他地方的時間更有意義,因為感覺同一時間能做很多事情。放鬆地坐著、思考、觀察、聆聽糞便從內往外移動的過程。
一隻蟑螂偷偷摸摸地躲在門縫裡,牠的觸角擺動著探路,接著整個身子露了出來。這隻蟑螂真漂亮,全身是一種華麗、高貴的棕色。蟑螂最獨特的是永遠不用凝視。他們自信到不需要使用眼睛。那隻蟑螂跌跌撞撞地往上爬,靠近鏡子。牠的幾隻腳謹慎而敏銳地動著。突然,牠一動也不動。一隻壁虎不知道從何處急疾地爬了過來,距離蟑螂約三個手掌時停了下來。蟑螂渺無聲息,只有觸角微微擺動。壁虎則扭動著尾巴。蟑螂就像人心果的核一樣飽滿,有光澤。壁虎果然是壁虎。我放棄,我無法把壁虎形容成其他東西。在兩隻動物之間的緊張時刻,糞便開始排出,歡暢,使人陶醉。我站起來,沖水之前還好奇地看了看糞便的樣子。總之是不錯的,形狀規則,長度適中,色澤也是健康的。順哥曾說糞便是健康最準確的指標。淙淙的沖水聲使雲璃昏昏地翻了翻身,短褲從她臉上滑落。
我記得我決定馬上回河內。雲璃反對。
我說:「妳想留下就留下,我才不要。」
雲璃委屈地嘟著嘴:「我還沒回家一趟呢!」
我並沒有阻止雲璃,她如果想就回家去一趟,我則已經待夠了。這是一個無聊的城市。我差點脫口而出說,真想對這座城市撒尿。
「你是不是想回到阿莊身邊?」
恣肆無忌的話讓我火大:「妳下次還這樣講話,我會撕爛妳的嘴,聽清楚了沒?!清楚了沒?!狗東西!」
最後我還是同意留下來等雲璃回家一趟。一個多小時後,她回來了。我問:「怎麼那麼快?」
雲璃說怕我等太久。撒謊。她家不怎麼富裕,她父母是礦工,哥哥是個重度的毒蟲,見誰都伸手要錢。這就是她從未在家裡停留超過三、四個小時的原因。
「還是我們今晚留下來?我還有個朋友,好久沒見面,我們晚上去找她玩。」 雲璃事不關己似的說著。
我把手機塞進褲袋裡,說:
「我他媽的好想對這個城市撒一泡尿。」
至今我都不懂為何忍了那麼久,最後還是把那句話吐了出來。雲璃因為家鄉受到侮辱而失落垂喪著臉。我特別討厭那些以家鄉為傲的人,那些同鄉會也令我覺得噁心。我們兩人擠上了首班的長途客運。我先跳上去,雲璃隨後上來,我並沒有留意她是否上來了。老實說我希望她會錯過這班車,回家陪陪父母。畢竟家庭仍是最安穩的地方。不過她似乎找到了比我更好的位置。我只能站在擁擠的人群當中,在黏稠而刺鼻的氣味中來回摸索。車子像一頭瘋牛一樣奔跑著、搖擺著、向前衝。透過某人的腋窩,我看見樹木、房屋、人和車飛速掠過。照這樣下去,遲早都會出事。我是這麼想的。到海陽省時,車子跟同一方向行駛的摩托車發生碰撞。我聽到刺耳的剎車聲,散發著燒焦味,伴隨著乾巴巴的巨大爆炸聲。全車人都往前傾倒。我下車時,看到那輛Way alpha牌的摩托車側翻在路邊,車尾稍微被壓扁,引擎仍然發出轟隆隆的聲音,後輪仍不停地轉動。
「看那裡!」 有人大喊。
我望向遠處,看到距離車頭近十公尺處有一堆灰色的東西。雲璃拉住我的手。我一把拖著她過去看。那是一個女人,她的頭折彎在腋下、臉色蒼白、嘴唇也毫無血色。看著那種詭異的躺姿,手腳疊在一起,我猜測沒有任何一根骨頭是完整的。唯獨一綹頭髮仍顯生機,每當微風吹過,髮絲輕輕飄動,彷彿撫摸著死者的臉龐。雲璃跑到路邊嘔吐。
我和雲璃換了一輛車,下午六點回到河內。
我約順哥去餐廳,每人喝了三杯啤酒,然後點了飯菜。我只夾了幾根蔬菜,配著白飯吃。看我對最愛吃的滷肉碰都沒碰,順哥很疑惑。等他吃完飯後,我才告訴他我不吃肉,是因為下午剛剛目睹了一場交通事故。順哥愣了一下,便扯開話題說剛找到一些有關渭川地區戰爭的俄文文獻,閒下來時會翻譯給我看。我脫口而出約他去那幾個省份玩。順哥搖頭。他對邊境不感興趣。他說過很多次,如果可以的話,人類應該齊心協力把這個世界輾平,這樣一來可以減輕麻煩。
「任何邊境都是危險的,他媽的最好避開。」
牽著車子準備回去時,順哥翻開那輛Spacy摩托車的坐墊拿出一本厚厚的書遞給我,並說了那句話。
當然,我像往常一樣點了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