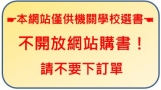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他們」,
被迫成為「中國人」。
◎「新疆」,如何「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地圖上的「新疆」,意思其實是「新的疆域」。是什麼時候新增的疆域?又是怎麼來的?她的另一個名字:「東突厥斯坦」,為什麼在中國是個禁忌?
事實上,要談新疆問題──不管是發生在新疆的各種暴力事件,或是疆獨問題、甚至是新疆的認同問題,都應該從「新疆」這個名字開始。這個宗教、文字與信仰都與普遍認定的「中國」大不相同的地方,從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開始,「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這個「新的疆域」走向分歧與動亂之路?
本書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在新疆遊歷十五年之久,可說親自見證在既存的文化差異下,中國政府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者,以及造成如今新疆本地的動盪,以及與內地漢人的衝突與歧見。
◎中國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份子?
居住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其實不管是在文化、宗教與語言上都與中國內地的漢人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在這樣的差異下,不論是在交流或溝通上都難免會產生齟齬。然而,面對這樣的差異,中國政府卻是以「同化」為前提,企圖達到「維穩」的效果。
因此,即使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維吾爾人的照顧,但霍史達克仍觀察到中國政府抹去維吾爾民族色彩的軌跡。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強迫穆斯林羞辱自己的宗教──包括把豬養在聖陵內。他們破壞清真寺,燒毀古蘭經。改革開放後,中國表面上大力保護穆斯林的文化,但在「去維吾爾」化的腳步卻越來越快;包括大量移入漢人、透過義務教育漸次以漢語取代維吾爾語。後者被看做是從根本抹去維族文化的手段之一;而在結合前者,讓漢人勢力在新疆逐漸站到經濟上的優勢後,許多的維吾爾年輕人因為無法在家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只好離開故鄉到中國內地謀生。而在投入一個陌生環境後必須面對的劣勢,則讓一部分人淪為中國內地人民口中的「維族小偷」、「新疆團夥」,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印記。
霍史達克在書中詳細描述:中國為了統治與維持局勢穩定而採行的多項政策如何造成衝突,這些衝突又如何演化為民怨;中國政府因此加強對新疆的諸多管制,這些管制則同步激化民怨。而在連番衝突下,漢人與維吾爾人如何走向彼此分岐與仇視之路;這些衝突、憤怒與仇視在日後成為極端主義者的溫床,也可說是一部分維吾爾人從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轉變為極端主義者的起點。
◎中國的新疆政策,該是台灣的借鏡嗎?
早在胡耀邦時期,中國便因為土耳其的插手而恐懼「將新疆拱手讓給土耳其」;而維吾爾的極端主義者多次引發的動亂,不但讓中國政府派重兵進駐新疆,更讓中國政府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視作恐怖組織。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維吾爾人對政治上的不公所採取的反擊──即使是社會案件──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是:更加強對新疆的管制。
中國從來沒有緩解像這樣衝突、民怨與分歧的機會嗎?胡耀邦曾經想為此努力過,卻被指稱為賣國。對「新疆可能獨立」與「外國勢力可能進入新疆」的恐懼,讓中國採取最激烈的統治手段。未來會有好轉的機會嗎?對此,在新疆遊歷了十五年的霍史達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對此抱持悲觀的理由,或許也該是台灣的借鏡。
推薦人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蔡偉傑 推薦‧審訂
好評推薦
「作為一位在該地區廣泛遊歷十五年之久的記者,霍史達克的書從一個罕見的角度為我們介紹這塊土地與人民的風貌,使我們了解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在維吾爾人間製造出極度的疏離感,及部分維吾爾人為何轉而採取激進手段及暴力。」--《海灣新聞》
「中國政府對其伊斯蘭邊境民族的壓制政策已經帶來嚴重惡果——在尼克霍史達克對新疆維吾爾族歷史做了重要的介紹後,我們了解北京政策是如何無意間催化出中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新政治家》
「在《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一書中,居於愛丁堡的作者尼克霍史達克開始為我們——套句中國共產黨的口頭禪——揭露新疆的『事實真相』,霍史達克的中心論點是: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所生活過的新疆有組織性的伊斯蘭恐怖行動或是廣泛的分離主義煽動,相反地,在過去幾年不斷增長的暴力事件本身就是對政府用以控制『恐怖行動』的壓迫性政策的反動——也就是說,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悲劇性地激起現在發生的一切作者的不偏不倚值得讚揚這本以一絲不苟的調查為基礎的作品絕對不只是耍耍嘴皮的抨擊中國而已。」--《十億民工進城來》作者唐米勒寫於《新政治家》中
「清楚透徹及最新的資訊尼克霍史達克使我們更深入了解新疆中國官方的防禦性及將這些外部議題政治化,雙管齊下的手段使得這個議題的對話幾乎遭到消音,希望尼克霍史達克的書和其他相似的作品能夠激起這種對話,如果沒有這樣的對話,那麼對新疆和中國的人民,及對該地區及更廣闊的世界來說,一個真實而持續悲劇將會繼續上演。」--凱利布朗,《開放民主》
「本書帶來許多深刻見解及豐富資訊記者霍史達克自二一年以來一直在新疆斷斷續續的旅遊及生活,他的文章會使任何為該地區撰文的人更加深入思考這個議題。」--喬納森米爾斯基於二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寫於《文學評論》
被迫成為「中國人」。
◎「新疆」,如何「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地圖上的「新疆」,意思其實是「新的疆域」。是什麼時候新增的疆域?又是怎麼來的?她的另一個名字:「東突厥斯坦」,為什麼在中國是個禁忌?
事實上,要談新疆問題──不管是發生在新疆的各種暴力事件,或是疆獨問題、甚至是新疆的認同問題,都應該從「新疆」這個名字開始。這個宗教、文字與信仰都與普遍認定的「中國」大不相同的地方,從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開始,「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這個「新的疆域」走向分歧與動亂之路?
本書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在新疆遊歷十五年之久,可說親自見證在既存的文化差異下,中國政府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者,以及造成如今新疆本地的動盪,以及與內地漢人的衝突與歧見。
◎中國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份子?
居住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其實不管是在文化、宗教與語言上都與中國內地的漢人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在這樣的差異下,不論是在交流或溝通上都難免會產生齟齬。然而,面對這樣的差異,中國政府卻是以「同化」為前提,企圖達到「維穩」的效果。
因此,即使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維吾爾人的照顧,但霍史達克仍觀察到中國政府抹去維吾爾民族色彩的軌跡。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強迫穆斯林羞辱自己的宗教──包括把豬養在聖陵內。他們破壞清真寺,燒毀古蘭經。改革開放後,中國表面上大力保護穆斯林的文化,但在「去維吾爾」化的腳步卻越來越快;包括大量移入漢人、透過義務教育漸次以漢語取代維吾爾語。後者被看做是從根本抹去維族文化的手段之一;而在結合前者,讓漢人勢力在新疆逐漸站到經濟上的優勢後,許多的維吾爾年輕人因為無法在家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只好離開故鄉到中國內地謀生。而在投入一個陌生環境後必須面對的劣勢,則讓一部分人淪為中國內地人民口中的「維族小偷」、「新疆團夥」,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印記。
霍史達克在書中詳細描述:中國為了統治與維持局勢穩定而採行的多項政策如何造成衝突,這些衝突又如何演化為民怨;中國政府因此加強對新疆的諸多管制,這些管制則同步激化民怨。而在連番衝突下,漢人與維吾爾人如何走向彼此分岐與仇視之路;這些衝突、憤怒與仇視在日後成為極端主義者的溫床,也可說是一部分維吾爾人從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轉變為極端主義者的起點。
◎中國的新疆政策,該是台灣的借鏡嗎?
早在胡耀邦時期,中國便因為土耳其的插手而恐懼「將新疆拱手讓給土耳其」;而維吾爾的極端主義者多次引發的動亂,不但讓中國政府派重兵進駐新疆,更讓中國政府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視作恐怖組織。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維吾爾人對政治上的不公所採取的反擊──即使是社會案件──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是:更加強對新疆的管制。
中國從來沒有緩解像這樣衝突、民怨與分歧的機會嗎?胡耀邦曾經想為此努力過,卻被指稱為賣國。對「新疆可能獨立」與「外國勢力可能進入新疆」的恐懼,讓中國採取最激烈的統治手段。未來會有好轉的機會嗎?對此,在新疆遊歷了十五年的霍史達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對此抱持悲觀的理由,或許也該是台灣的借鏡。
推薦人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蔡偉傑 推薦‧審訂
好評推薦
「作為一位在該地區廣泛遊歷十五年之久的記者,霍史達克的書從一個罕見的角度為我們介紹這塊土地與人民的風貌,使我們了解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在維吾爾人間製造出極度的疏離感,及部分維吾爾人為何轉而採取激進手段及暴力。」--《海灣新聞》
「中國政府對其伊斯蘭邊境民族的壓制政策已經帶來嚴重惡果——在尼克霍史達克對新疆維吾爾族歷史做了重要的介紹後,我們了解北京政策是如何無意間催化出中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新政治家》
「在《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一書中,居於愛丁堡的作者尼克霍史達克開始為我們——套句中國共產黨的口頭禪——揭露新疆的『事實真相』,霍史達克的中心論點是: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所生活過的新疆有組織性的伊斯蘭恐怖行動或是廣泛的分離主義煽動,相反地,在過去幾年不斷增長的暴力事件本身就是對政府用以控制『恐怖行動』的壓迫性政策的反動——也就是說,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悲劇性地激起現在發生的一切作者的不偏不倚值得讚揚這本以一絲不苟的調查為基礎的作品絕對不只是耍耍嘴皮的抨擊中國而已。」--《十億民工進城來》作者唐米勒寫於《新政治家》中
「清楚透徹及最新的資訊尼克霍史達克使我們更深入了解新疆中國官方的防禦性及將這些外部議題政治化,雙管齊下的手段使得這個議題的對話幾乎遭到消音,希望尼克霍史達克的書和其他相似的作品能夠激起這種對話,如果沒有這樣的對話,那麼對新疆和中國的人民,及對該地區及更廣闊的世界來說,一個真實而持續悲劇將會繼續上演。」--凱利布朗,《開放民主》
「本書帶來許多深刻見解及豐富資訊記者霍史達克自二一年以來一直在新疆斷斷續續的旅遊及生活,他的文章會使任何為該地區撰文的人更加深入思考這個議題。」--喬納森米爾斯基於二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寫於《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