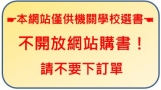有牠們的存在,才有現在的我們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澳洲野犬是全人類的祖先。
起初存在的只有半人半狗的生物,之後才開始有的變成狗,有的變成人。
澳洲野犬的父母變成原住民,白狗變成白人的小孩。」
-老提姆,澳洲原住民耆老
生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後成為人類學家,田野做的是澳洲原住民,作者黛博拉?羅斯的研究成果與成長經驗無法調和。
基督宗教中的上帝曾以人的形象來到世界,經歷人類的種種限制,作為上帝肉身之愛的顯現,這樣的信仰設定千年來未曾動搖。然而人類卻愈來愈孤獨,現代化導致的分離與寂寞,與這時代亮眼的科技表現並存,在崇拜進步之神的同時,也釋放了好戰的鬥犬,而那好戰的鬥犬似乎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痛苦、寂寞,並質疑存在的意義。
在澳洲原住民的世界觀中,把澳洲野犬視為全人類的祖先:死亡的經驗和死後的遭遇、主宰的慾望、無以回報的恩德、人與其他生物之間深遠的連結,都是人類與澳洲野犬親緣關係最有力的表現。然而,澳洲政府與民間無視其重要性,正大規模濫殺無辜。作者長期在田野中與澳洲原住民一同生活,在逐漸深入了解原住民的世界觀的同時,也對她基督宗教的世界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澳洲野犬是全人類的祖先。
起初存在的只有半人半狗的生物,之後才開始有的變成狗,有的變成人。
澳洲野犬的父母變成原住民,白狗變成白人的小孩。」
-老提姆,澳洲原住民耆老
生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後成為人類學家,田野做的是澳洲原住民,作者黛博拉?羅斯的研究成果與成長經驗無法調和。
基督宗教中的上帝曾以人的形象來到世界,經歷人類的種種限制,作為上帝肉身之愛的顯現,這樣的信仰設定千年來未曾動搖。然而人類卻愈來愈孤獨,現代化導致的分離與寂寞,與這時代亮眼的科技表現並存,在崇拜進步之神的同時,也釋放了好戰的鬥犬,而那好戰的鬥犬似乎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痛苦、寂寞,並質疑存在的意義。
在澳洲原住民的世界觀中,把澳洲野犬視為全人類的祖先:死亡的經驗和死後的遭遇、主宰的慾望、無以回報的恩德、人與其他生物之間深遠的連結,都是人類與澳洲野犬親緣關係最有力的表現。然而,澳洲政府與民間無視其重要性,正大規模濫殺無辜。作者長期在田野中與澳洲原住民一同生活,在逐漸深入了解原住民的世界觀的同時,也對她基督宗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