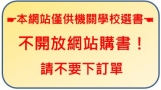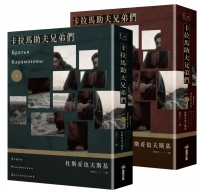深刻影響著卡夫卡、海德格、維根斯坦、愛因斯坦等偉大心靈
重新還原翻譯名家耿濟之開山譯作
專文收錄赫曼赫塞,<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或歐洲的沒落:讀杜斯妥也夫斯基有感>
毛姆,<費奧多.杜斯妥也夫斯基及其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荒誕在這地上實在太必要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誕之上……
──節錄自<叛逆>
你們應該愛上帝創造的一切東西,整體和每粒沙子。愛每張樹葉、每條上帝的光。愛動物、愛植物,愛一切的事物。你如愛一切的事物,便能理解上帝在事物裡的祕密。一旦有了理解,便可每天無休止地得到越來越多的認識。你終於將用整個的、全世界的愛,來愛全世界。
...
我們這世紀,大家全分成單位,每個人都隱進自己的洞穴裡面,每人互相隔離,互相躲藏,把自己所有的藏起來,結果是弄得被人們推開,自己又去推開人們……現在人類的智性已到處開始懷著訕笑,不願瞭解,個性的真正保障並不在於孤立的、個性的努力,而在於社會的合群。
──節錄自<俄羅斯的僧侶>
上帝是否存在?
人類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你是否願意將人類永恆的和平建立在少數人的痛苦犧牲?
假使上帝並不存在,「一切都是許可的」,那麼在這一個無規則可言的荒誕之中,我們該如何生活著?
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開啟了存有問題的濫觴,將人性各種面向的可能,與人性之間的愛恨對立拉伸到極致。一個悲劇性的家庭是如何演變為弒父慘案,心靈該如何才能避免走向邪惡與虛無一途?在這部巨著,一切的病態與精神失常都是合理的,皆背負著它們的時代特徵,故事中的腳色不僅像是活生生的人,更是人類精神的深刻剖析。作者像是預先為每位讀者安放了專屬於他們的位置,只待人們在旅途中享受一場場價值辯證的洗禮,並將讀者帶向何謂善、何謂真理、何謂生活的永恆謎題……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是史上最宏大的小說。」
──佛洛伊德
「格里帕策、杜斯妥也夫斯基、克萊斯特、福樓拜,我認為這四位是我真正的血親。」
──卡夫卡
「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罪犯、瘋子和白癡,截然不同於其他小說中的罪犯或瘋子。我們是如此恐懼地理解他們、如此奇特地愛著他們,在我們自身上發現與他們契合與相似之處。」
──赫曼.赫塞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你可以稱之為瘋狂,但或許這就是他天才的祕密......所有偉大的人都有這種傾向,這是他們偉大的源泉。理智的人一事無成。」
──喬伊斯
「一切皆是許可的」,伊凡.卡拉馬助夫呼喊道。這句話聽起來很荒謬,但前提是它不能以一般的意義來理解。我不知道是否已足夠地強調了這一點,意即這吶喊並不是一種解脫或歡欣的爆發,而是對某一個事實的痛苦認知。相信一個能給予生命意義的上帝,比能夠不受懲罰地行惡,更要吸引人。選擇並不困難。但選擇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痛苦所在。
──卡繆,摘錄自《薛西弗斯的神話》
重新還原翻譯名家耿濟之開山譯作
專文收錄赫曼赫塞,<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或歐洲的沒落:讀杜斯妥也夫斯基有感>
毛姆,<費奧多.杜斯妥也夫斯基及其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荒誕在這地上實在太必要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誕之上……
──節錄自<叛逆>
你們應該愛上帝創造的一切東西,整體和每粒沙子。愛每張樹葉、每條上帝的光。愛動物、愛植物,愛一切的事物。你如愛一切的事物,便能理解上帝在事物裡的祕密。一旦有了理解,便可每天無休止地得到越來越多的認識。你終於將用整個的、全世界的愛,來愛全世界。
...
我們這世紀,大家全分成單位,每個人都隱進自己的洞穴裡面,每人互相隔離,互相躲藏,把自己所有的藏起來,結果是弄得被人們推開,自己又去推開人們……現在人類的智性已到處開始懷著訕笑,不願瞭解,個性的真正保障並不在於孤立的、個性的努力,而在於社會的合群。
──節錄自<俄羅斯的僧侶>
上帝是否存在?
人類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你是否願意將人類永恆的和平建立在少數人的痛苦犧牲?
假使上帝並不存在,「一切都是許可的」,那麼在這一個無規則可言的荒誕之中,我們該如何生活著?
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開啟了存有問題的濫觴,將人性各種面向的可能,與人性之間的愛恨對立拉伸到極致。一個悲劇性的家庭是如何演變為弒父慘案,心靈該如何才能避免走向邪惡與虛無一途?在這部巨著,一切的病態與精神失常都是合理的,皆背負著它們的時代特徵,故事中的腳色不僅像是活生生的人,更是人類精神的深刻剖析。作者像是預先為每位讀者安放了專屬於他們的位置,只待人們在旅途中享受一場場價值辯證的洗禮,並將讀者帶向何謂善、何謂真理、何謂生活的永恆謎題……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是史上最宏大的小說。」
──佛洛伊德
「格里帕策、杜斯妥也夫斯基、克萊斯特、福樓拜,我認為這四位是我真正的血親。」
──卡夫卡
「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罪犯、瘋子和白癡,截然不同於其他小說中的罪犯或瘋子。我們是如此恐懼地理解他們、如此奇特地愛著他們,在我們自身上發現與他們契合與相似之處。」
──赫曼.赫塞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你可以稱之為瘋狂,但或許這就是他天才的祕密......所有偉大的人都有這種傾向,這是他們偉大的源泉。理智的人一事無成。」
──喬伊斯
「一切皆是許可的」,伊凡.卡拉馬助夫呼喊道。這句話聽起來很荒謬,但前提是它不能以一般的意義來理解。我不知道是否已足夠地強調了這一點,意即這吶喊並不是一種解脫或歡欣的爆發,而是對某一個事實的痛苦認知。相信一個能給予生命意義的上帝,比能夠不受懲罰地行惡,更要吸引人。選擇並不困難。但選擇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痛苦所在。
──卡繆,摘錄自《薛西弗斯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