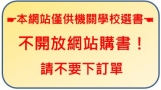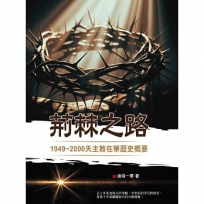【本書簡介】
本書探討1949至2000年間天主教在華歷史的發展演變。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因其秉承馬列主義無神論思想,對各宗教皆持否定態度。基督信仰因其與西方世界的緊密聯繫,更是成為政權重點關注對象。本書從共產主義思想淵源談起,分析並比較蘇俄及東歐共產政權對於教會政策的制定、實施,及對中共宗教政策的影響,乃至其間教會與共產主義的互動與衝突。
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強化對宗教的改造。天主教會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在中共統戰策略的運用下,內部出現了分裂。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建立、自選自聖主教的出現,撕裂了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合一共融。但在半個世紀的浮沉中,中國教會內部亦湧現出了為數眾多堅持信仰原則的忠貞牧者與信友,他們的犧牲與奉獻,是對基督福音有力的見證。
本書以時間為主軸,結合當時政治及社會背景,探討教會面臨的挑戰。幫助讀者從另一視角來瞭解教會在這五十年間的坎坷艱辛,從而對今日的中國教會現狀有所反思。
【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滄海一粟——旅外歷史學者.
【推薦序】
廿世紀下半頁的中華教會歷史跌宕起伏,其面臨的挑戰與苦難不容遺忘。天主教會在華的境遇是自百年禁教以來,最為複雜的一個時期。與以往歷代王朝不同的是,教會此時面臨著一個崇奉無神論的政黨所建立的政權,這一政權建立起以黨統政,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一切都要在黨的完全掌控下。宗教團體本就是執政黨懷疑的對象,天主教因其特殊的背景更是被政權視為潛在的威脅,進行了多層次的監督改造。教會在這此過程中曾有過抗爭,也曾試想與政權妥協,但由於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雙方終究難以取得互信。
希望藉由這錯綜複雜的五十年(1949~2000)歷史反省,能夠讓我們從中領會到經驗教訓,適時調整與放慢腳步,聆聽聖神的引導,要相信「時間屬於祂,歷史屬於祂,光榮和權能也歸於祂,直到永遠」。
【作者序】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天主教在華歷史,可謂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教會所經歷的挑戰與困難在普世教會歷史中亦屬罕見。中國教會在政治勢力的裹挾下,艱難度日。教會領袖與信徒在無神論政權統治下,在凱撒和天主之間面臨抉擇。在堅守信仰原則或謀求生存空間這一問題上,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中國教會也出現了裂痕,兩個團體之間一度關係緊張。教會在這半世紀的時光中,在這條布滿血與淚的荊棘之路上舉步維艱,猶如基督當年所走的苦路一般。五十年來湧現出無數敢於為信仰作證的勇士,他們的勇敢與犧牲是福音精神的體現,也是中國教會能夠生存發展的精神財富。
這段歷史長久以來由於其高度的敏感性與複雜性,國內外學者少有涉及。在寫作過程中,筆者有時亦感困難重重。首先,由於中國境內環境特殊,很多檔案資料無法查閱,只有期待未來檔案解密能夠彌補本書不足;其次,許多事件當事人懾於外部環境,對於當年所經歷之事語焉不詳。這些原因影響了本書的主題研究,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本書的完成,參考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感謝。希望本書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之效。而在倉促之中,書中文字表述難免會有謬誤之處,歡迎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目錄】
第一章 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的相遇
第二章 中共宗教理念與實踐
第三章 政治運動下的天主教會
第四章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4~1959)的天主教會
第五章 階級鬥爭為綱時期(1960~1970年代)的天主教會
第六章 後文革時期的天主教會
第七章 改革開放年代的天主教會(1980~2000)
結 語
附錄一:1949~2000中國教會史大事年表
附錄二:中央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
附錄三:教宗譴責愛國會《宗徒之長》通諭(1958.06.29)
參考文獻
【內容試讀】
第一章
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的相遇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伊始,如何處理對外關係成為中共重要工作之一。天主教、基督教(新教)[ 華語世界中基督教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基督宗教泛指所有信奉耶穌基督為救主的教會涵蓋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狹義上則專指宗教改革後從天主教中分裂出的新教各派。] 這兩個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的宗教團體,被中共視為威脅政權穩定的隱患;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是中共建政初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作為一個信奉馬列主義且具有鮮明無神論色彩的政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多種宗教流傳的國度,如何鞏固起新建立的政權,考驗著中共的政治智慧。
一、共產主義對於宗教的看法
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敵視一切宗教。馬克思本人認為「宗教是顛倒了的世界觀」,「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1995),1~2頁。] 宗教與鴉片等同,一切宗教都是毒品,成為共產主義者信奉的圭臬。恩格斯在1878年《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1995),354頁。] 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宗教隨著私有制的消亡,也會自然消亡,雖然這一計畫是長期性的。宗教的作用是負面消極的。恩格斯譴責天主教會:「封建制度的巨大國際中心是羅馬天主教會。它把整個封建的西歐(儘管有各種內部的戰爭)聯合為一個大的政治體系。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 同上,390頁。] 在十九紀資產階級時代,統治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響群眾的精神手段中,第一個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 同上,401頁。]
十九世紀在歐洲基督宗教社會主義曾經流行一時,認為早期教會中的團體生活---彼此互助、財產公有---是共產主義的前驅;但馬克思、恩格斯對此強烈反對,並刻意和基督宗教社會主義劃清界限,甚至明言:「法國共產主義者最喜歡的一個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產主義。他們竭力想用聖經,用最早的基督教徒過的公社式的生活等來證明這個公式。可是這一切只是說明了,這些善良的人們絕不是最好的基督教徒,儘管他們以此自居。因為他們如果真是最好的基督教徒,那他們對聖經就會有更正確的理解,就會相信即使聖經裡有些地方可以作有利於共產主義的解釋,但是聖經的整個精神是同共產主義、同一切合理的創舉截然對立的。」[《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583頁。]
為了反駁基督教社會主義,恩格斯在1894年發表《論早期基督教歷史》,指出教會所追求完美世界是在死後的天堂,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則是追求現世的解脫,打造所謂的人間樂園,這是兩者的本質區別。為了削弱宗教的影響,必須將教會從教育和社會服務領域驅逐,取消國教,實行「政教分離」,從而加速宗教的衰落。馬克思、恩格斯對於宗教的批判,僅局限於理論層面,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建立第一個以馬克斯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俄共在其領袖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的領導下,將馬克思主義反宗教理念進一步發展,並且藉由國家機器推行嚴厲的反宗教措施,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反宗教運動。
二、蘇聯的消滅宗教實踐
蘇俄共黨首領列寧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宗教問題著作選編及講解》(北京:宗教文化,1999),155頁。] 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其世界觀是絕對的無神論,與宗教世界觀是完全對立的。要對一切宗教展開堅決鬥爭,強化無神論的宣傳,但出於革命需要,在一定時期內要利用分化宗教團體中的力量,運用統戰策略,在共產黨處於劣勢時期,要和不同宗教團體展開合作,在合作中「我們永遠要宣傳科學的世界觀,我們必須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徹底性進行鬥爭。」[ 同上,147頁。] 宗教信仰並不是個人私事,「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並不是私人的事情。我們的黨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覺悟的先進戰士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對信仰宗教這種不覺悟、無知和蒙昧的表現置之不理。對我們來說,思想鬥爭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 同上,145頁。]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列寧發展了一套比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更加激進的理論,在實踐中則是直接以國家暴力摧毀宗教。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消滅宗教的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首當其衝的就是在俄羅斯擁有悠久歷史的東正教會。
自988年基輔羅斯受洗後,斯拉夫人與東正教會形成了緊密的聯繫。尤其是沙皇俄國時期,東正教處於國教的地位,享有各種優越的條件。蘇俄政權建立後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蘇俄政權發布《土地法令》,宣布沒收「寺院、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鄉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土地將「一律無償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權,成為全民財產並交給一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譯,《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0),8頁] 取消宗教婚姻的合法性,只承認世俗婚禮的有效性。1918年1月23日,頒布《政教分離》法令,依據該法令,「教會同國家分離,每個公民都有權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戶籍工作只由民政機關,即婚姻和出生登記處辦理,剝奪過去教會所負責的事務,學校同教會分離,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不給予任何特權和津貼,凡在俄國屬於教會和宗教團體的全部財產都宣布為人民的財產,專供祈禱用的建築物和物品也只能根據地方和中央國家政權機關的特別規定,轉交有關宗教團體無償使用。」[ 同上,18~20頁。] 法令事實上剝奪了教會所有產業,含動產與不動產,使其難以在社會立足,加速其衰落。
在思想文化領域,加強無神論的宣傳,成立戰鬥的無神論組織,該組織在全國設立分支機構。列寧在1922年發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宣傳無神論思想,成立專門的雜誌,系統翻譯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來各類鼓吹無神論思想的書籍。在俄共中央成立反宗教委員會和國家與教會分離委員會,指導各地消滅宗教運動。1922年3月19日,列寧致函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中,提及展開沒收教會珍寶運動,特別指出:
我們務必通過最堅決、最迅速的方式,去沒收教會的珍寶,這樣我們才能獲得幾億盧布。為了達到某一政治目標,必須採用一系列殘酷的手段,那就應該用最堅決的方式在最短時間裡實施。我們正是應該在現在最堅決、最無情地向黑幫神職人員開戰,十分殘酷地鎮壓他們的對抗,要讓他們幾十年也忘不了。委派一名精幹的、擅長指揮全俄中央執委會成員或中央政權代表去舒亞(城市名),通過政治局五名委員給他下達口頭指示,要盡可能多地逮捕當地神職人員、小市民和城市資產階級代表,要以最快的速度審訊,審訊結束時,要槍決其中的黑幫分子……如有可能,還要槍決莫斯科和其他幾個宗教中心的黑幫分子。[〈列寧關於沒收教會珍寶致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信〉,1922年3月19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北京:社科文獻,2002),411~414頁。]
通過蘇聯檔案顯示,列寧的暴力指示非常明顯將矛頭指向一切反抗徵用教會珍寶的神職人員。所謂的教會珍寶即是歷代沙皇貴族以及百姓對與教會的捐贈,主要用於裝飾聖像、苦像及聖髑,在蘇俄共黨中央指揮下,大量教堂及修道院被劫掠摧毀,神父及修士們被流放及屠殺。1922年3月20日俄共國家政治保衛局副局長溫什利克特向政治局彙報建議:「現在逮捕東正教最高會議成員和大牧首是適時的……必須將所有強烈反對徵收財寶的神父和教徒送往饑餓的波沃爾日耶最饑餓的地區,在那裡將他們作為人民的敵人在當地饑餓的居民面前示眾。」[ 〈溫什利克特關於宗教界由於沒收教會珍品而進行活動的報告〉,1922年3月20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北京:社科文獻,2002),423頁。] 在經歷所謂獻寶運動後,從教會沒收的財寶「黃金總計442公斤,白銀336227公斤,其他貴重金屬1345公斤,重13.13克拉的鑽石33456粒,珍珠4414克,其他貴重寶石共72383塊,重28140克,硬幣20598盧布」[[俄]赫克著,高驊、楊繽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1999),72頁。]。
透過對教會產業的掠奪,使得教會一貧如洗,藉此清洗一批敢於反抗的神職人員,以反革命罪名監禁處決教會領袖。炮製「吉洪案件」[ 吉洪(Тихон,1865~1925)為當時俄羅斯東正教最高領袖,第十一任牧首。他反對蘇維埃政權對於東正教會的迫害政策,為蘇俄當局所不容,被蘇維埃政權逮捕審訊,1925年死於監禁中。他被東正教視為為信仰而死的殉道者,1989年俄羅斯東正教為其舉行了封聖典禮,尊稱其為聖吉洪。],分化東正教神職與信徒關係,扶植一批「進步神職人員」向黨中央請願,懲治教會中反蘇維埃神職與信徒,擁護蘇俄反宗教法令。這些「進步神職人員」譴責教會高層站在階級敵人的這一面,配合國際上反蘇反共的論調,譴責牧首吉洪「妄圖阻撓沒收教會珍品賑濟災民的行動,妄圖掀起民眾暴亂,扼殺與他們不共戴天的蘇維埃政權。」[《彼得格勒等地「進步神職人員」團體致俄羅斯東正教徒的呼籲書》,1922年5月10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北京:社科文獻,2002),451頁。] 他們假借教會的名義,來批鬥東正教會,這種手法,為後來很多共產政權所繼承。
三、史達林時期的宗教政策
1924年1月21日列寧去世,但是反宗教的措施並沒有終止。列寧死後,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在經歷了殘酷的黨內鬥爭後,成為新的領袖,他是蘇聯歷史上掌權最久的領導人,施政風格比列寧更加暴力殘忍,無論是席捲全俄的大清洗運動,還是對於異議人士的迫害,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1929年開始加速工業化的政策,提高鋼產量成了蘇聯各級政府的重要目標,也成了另一輪打擊宗教運動的開始,著名的砸大鐘運動拉開了序幕,各地教堂的鐘成為了掠奪的目標。當局認為教堂的鐘聲是舊時代的產物,影響了勞動人民的休息與生活,應該拆除熔煉,為國家工業化做出貢獻。
1930年開始,俄共中央政治局下令開始全面拆除教堂鐘樓,拒絕者將教堂一併拆除,僅從「謝爾吉耶夫聖三一修道院一處就獲得19口大鐘,合8165普特(130噸),熔化燭臺、枝形燭臺、神幡、洗禮盆、銅柵欄及各種裝飾物獲得約10噸有色金屬。莫斯科自1929年開始陸續封閉了30~50間教堂,每間教堂都『提供』了大量銅。比如『金屬公司』員工在1929年被關閉的大謝爾普霍夫耶穌升天教堂拆鐘14口、重達17噸;莫斯科河南岸區的聖凱薩琳教堂拆鐘21噸;1930年被關閉的阿列克西都主教教堂拆鐘10噸。」[ 厭然閒居譯,〈工廠拔地起,教堂鐘鳴息〉,2019年9月9日載於https://sanlier.blog/2019/09/09/%E5%B7%A5%E5%8E%82
%E6%8B%94%E5%9C%B0%E8%B5%B7%EF%BC%8C%E6%95%99%E5%A0%82%E9%92%9F%E9%B8%A3%E6%81%AF/] 蘇聯冶金工業部也制定五年計畫來拆除各地教堂的大鐘。蘇聯輿論也假借人民聲音,對於這場荒謬測運動大唱讚歌:
我們是最後聽過教堂鐘鳴的人。從今往後,傍晚的鐘聲、貴族的詩歌、復活節時教堂的胡言亂語、送別死者時陰森森的哀樂都將遠離我們的子孫。教會啞然,宗教入土,末了的鐘聲乃是宣告他們千年統治終結的喪鐘。而銅鐘經過無神論者冶煉廠的洗禮,也會唱起讚美勞動之響亮頌歌,機器運轉的雄偉節奏取代了昔日孱弱的祈禱鐘鳴。[ 同上。]
1926年蘇聯頒布新《刑法典》,對於宗教活動做出了嚴格限制與懲罰措施,規定任何人「在國立和私立學校中向幼年人和未成年人傳授東正教教義,或是違犯此項法律的,判處一年以下勞動改造;為教會或宗教團體的利益而強迫募捐者,判處6個月以下勞動改造或300盧布以下罰金;宗教或教會組織擅自利用行政、審判或者其他公法上的職權,和擅自行使法人權利者,判處6個月以下勞改或300盧布以下罰金;在國家或公共機關、企業中舉辦宗教儀式,或者在上述機關、企業中懸掛某種宗教畫像者,要判處3個月以下勞改或300盧布以下罰金;對以宗教信仰或其他個人信仰為藉口,拒絕或逃避服義務兵役者,要判處剝奪3年以下的自由。」[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917~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132頁。]
通過嚴刑峻法,縮小宗教生存空間,許多神職人員在無意中就觸犯了刑法而被監禁、勞改、流放。史達林執政時期,堅持拆除教堂,在首都莫斯科周邊地區,「克里姆林宮內的丘多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大教堂,幾乎『中國城』內的大部分教堂、西蒙諾夫修道院的大部分建築、紅場旁邊的契爾文斯基聖母小教堂和其他許多教堂都被搗毀。」[ 同上,134頁。] 最具代表性的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於1931年被用炸藥摧毀,並在原址上建立游泳館;這座教堂是為紀念1812年戰勝拿破崙入侵而建立,裡面收藏了大量歷史文物,這樣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教堂,最終也難逃被拆除的命運。
史達林認為拆毀教堂只是表面上消滅宗教,只有把宗教從人的思想意識中消除,才是真正的消滅宗教。神職人員與教徒是傳播宗教的主體,必須要從整體上消滅神職階層,可以借用分化方式,利用「進步神職人員」打擊所謂落後人員,待時機成熟後再一網打盡,包括「進步神職人員」也在被消滅的行列之內。在大清洗[ 11930年代,蘇共領袖史達林發動的政治清洗運動,從打擊黨內政敵,擴大到對軍隊、知識份子、黨外人士、宗教人士的大屠殺。從1936~1938年間,約有70~120萬人死於清洗運動。]之前,蘇聯一直推動內部消滅政策。1934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1934)遇刺身亡,他的死成了大清洗的導火索,為了深挖所謂階級敵人,史達林下令逮捕一批神職人員。1936年大清洗全面開展,三年內幾乎全部的主教及神父都被逮捕關押。1939年全蘇教堂數量減少三分之一,剩餘的教堂大多數也被該做倉庫廠房,用作宗教用途寥寥無幾,殘留開放的教堂僅供外國人參觀而被保留下來。[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34頁。]
殘留的東正教領袖們開始向蘇共妥協。1927年牧首謝爾蓋發表宣言,表示要做奉公守法的公民,呼籲流亡海外的俄羅斯正教會的神職與信徒承認蘇維埃政權,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壓力之下的被迫服從,縱使謝爾蓋牧首積極配合蘇聯各項活動,在大清洗中也飽受折磨,只是由於他對外代表俄羅斯東正教發言維護蘇聯當局的宗教迫害政策,才得以保全性命。其他主教們則沒有那麼幸運,35名總主教被處決或人間蒸發。彼得格勒地區神職人員1937年比1936年較少一半,由79人銳減為25人。[ 同上,156頁。]
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不僅對東正教是毀滅性的打擊,其他宗教比東正教處境更為悲慘。天主教會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被視為外國人的宗教團體,與東正教相比多了一份原罪,在反對蘇維埃政權罪名外,往往被扣上帝國主義間諜的罪名,蘇聯境內天主教全部主教們都被逮捕,流放處決,聖統制瀕於滅亡邊緣。教宗庇護十一世極為關心俄羅斯天主教信友狀況,曾經多次呼籲國際社會關心蘇聯境內宗教狀況,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廣泛回應,也讓蘇聯當局憂心忡忡。
為了挽救俄羅斯教會聖統不被滅絕,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法國耶穌會士赫爾比尼神父(Michel-Joseph Bourguignon dHerbigny,1880~1957)為主教,赴莫斯科暗中重建教會組織,赫爾比尼主教先後建立九個宗座署理區,秘密祝聖了四位主教。[ 四位主教分別為:Pie Eugène Neveu(1877~1946),法國聖母升天會會士,任命為莫斯科宗座署理,1926年4月21日秘密祝聖。Aleksander Frison(1875~1937)生於烏克蘭的德國移民後裔,1926年5月10日任命為奧德薩(Odessa)宗座署理。Boļeslavs Sloskāns(1893~1981),拉脫維亞人,1926年5月10日與Aleksander Frison一起接受主教祝聖,任命為明斯克(MInsk)宗座署理。Antoni Malecki(1861~1935),波蘭人,彼得格勒(聖彼德堡)宗座署理。] 但是在蘇聯當局殘酷的迫害政策下,幾位主教先後被逮捕驅逐,蘇聯境內天主教會一度和教廷失去聯繫。尤為悲慘的是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徒[ 1596年布列斯特會議上烏克蘭和部分白俄羅斯東正教徒改宗羅馬天主教,獲得了時任教宗克萊孟八世(Clemens VIII,1592~1605在位)批准,形成了烏克蘭希臘禮(拜占庭禮)教會,為天主教東方禮教會之一,依據2020年資料烏克蘭希臘禮信徒482萬,占烏克蘭總人口11.52%。資料來源於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Church 2020(Vatican City: Librera Editrice Vaticana, 2022)。]:在1920~1930年代的迫害中,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被流放;二戰後,1946年又被蘇聯當局強行合併與東正教,2700多所堂區被侵佔,數百萬拒絕服從的信徒轉入地下狀態。
1924年底,俄共中央委員會反宗教委員會制定蘇聯天主教條例,對天主教從組織制度、禮儀、語言、教堂的所有權,及神職人員的產生,做了嚴格的要求:「禁止天主教任何修會團體在蘇聯活動,禮儀必須用拉丁語,禁止成立慈善組織,教宗通諭及其他檔案必須由蘇聯政府審查批准後方可發行,主教和司鐸的調動要經蘇聯政府批准,蘇聯政府有權對於主教候選人進行審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反宗教委員會提出的關於蘇聯天主教基本條例草案〉,1924年12月9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卷,650頁。] 蘇共當局視羅馬為反蘇天主教精神中心,開動各種宣傳工具來反對教會;在發行的各類商品包裝上,也要印刷反宗教的宣傳,著名的宣傳有:「教士就是我們的生死仇人!用兩隻眼牢牢瞪住他要緊。讓我們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來答覆教皇的誣衊謗陷,用文化趕跑宗教和酒精。」[ 赫克著,高驊、楊繽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349頁。]
1917年十月革命前,生活在沙皇統治下的穆斯林人數近2000萬,主要生活在中亞地區。伊斯蘭教教義及法律在中亞穆斯林聚居區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建立起系統的教法學校,為穆斯林兒童提供宗教教育,這類學校實際上也扮演著教化功能,解決了穆斯林基本教育問題。十月革命後,列寧認為這類學校存在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號召黨員幹部要與這類泛伊斯蘭主義作鬥爭,關閉宗教學校。雖然黨內有人認為不應該驟然取消穆斯林宗教學校,而應開辦世俗學校與宗教學校並行,用政策鼓勵穆斯林學生進入世俗學校學習;但這一主張並沒有被黨內接納。1919年在中亞穆斯林聚居區展開了關閉宗教學校、清真寺,並沒收教產等活動,引發了穆斯林社會強烈不滿,爆發了「巴斯馬奇運動」[ 巴斯馬奇運動,是指中亞地區穆斯林為反抗蘇聯的消滅伊斯蘭教運動,而爆發的武裝反抗運動,延至1920年代末才被徹底鎮壓。]。
面對穆斯林的激烈反抗,史達林採取了支持穆斯林中的「進步分子」打擊反動穆斯林,聯共(布)中央[ 蘇聯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稱呼之一,其前身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布爾什維克派;十月革命後,1918年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1925年改稱全聯盟共產黨,簡稱聯共布;1952年聯共布十九大上,改黨名為蘇聯共產黨。]宣傳部發布關於與穆斯林宗教運動鬥爭的草案,要求採取司法懲罰與司法外的措施來鎮壓反動穆斯林宗教界,關閉穆斯林宗教學校,關閉清真寺,穆斯林教職人員被劃分為富農階級,沒收財產,流放西伯利亞地區勞改。穆斯林學校的關閉,世俗學校無法滿足眾多兒童求學問題,導致大量兒童失學。在土庫曼斯坦地區,世俗學校只能收容9%學齡兒童,整體中亞穆斯林聚居區,世俗學校只能提供15%~16%學齡兒童入學。[ 邵麗英,〈蘇聯在中亞伊斯蘭教政策的歷史嬗變〉,《中東問題研究》2017年第1期,218頁。] 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以暴力拆除清真寺,強迫穆斯林交出一切生產工具,家畜加入集體農莊。清真寺數量急劇下降,在烏茲別克地區十月革命前,清真寺數量14905座,到1936年僅剩4830座;塔什干地區不足革命前三分之一;舍拉巴茨克地區革命前有101座清真寺,到1936年則全部被摧毀。[ 同上,219頁。]
蘇聯境內的佛教徒,主要是自沙俄時代即生活在布里亞特(Buryatia)、卡爾梅克(Kalmykia)及唐努圖瓦(Tannu Tuva)三個自治共和國蒙古人的後裔,他們主要信奉藏傳佛教的格魯派。「1916年布里亞特大約34所寺院及15000名喇嘛,卡爾梅克有70所寺院及1600名喇嘛,1923年增長為2840名。在唐努圖瓦總人口6萬人中共有22所寺廟,2000名喇嘛。」[ Hans Braker, "Buddh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nihilation or Survival?”,1980年10月3日,https://biblicalstudies.org.uk/pdf/
rcl/11-1_036.pdf] 這些信奉佛教的地區在十月革命後,尚未受到反宗教運動的波及;但隨著內戰的結束及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俄共中央開始了針對佛教的打擊運動。……
本書探討1949至2000年間天主教在華歷史的發展演變。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因其秉承馬列主義無神論思想,對各宗教皆持否定態度。基督信仰因其與西方世界的緊密聯繫,更是成為政權重點關注對象。本書從共產主義思想淵源談起,分析並比較蘇俄及東歐共產政權對於教會政策的制定、實施,及對中共宗教政策的影響,乃至其間教會與共產主義的互動與衝突。
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強化對宗教的改造。天主教會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在中共統戰策略的運用下,內部出現了分裂。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建立、自選自聖主教的出現,撕裂了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合一共融。但在半個世紀的浮沉中,中國教會內部亦湧現出了為數眾多堅持信仰原則的忠貞牧者與信友,他們的犧牲與奉獻,是對基督福音有力的見證。
本書以時間為主軸,結合當時政治及社會背景,探討教會面臨的挑戰。幫助讀者從另一視角來瞭解教會在這五十年間的坎坷艱辛,從而對今日的中國教會現狀有所反思。
【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滄海一粟——旅外歷史學者.
【推薦序】
廿世紀下半頁的中華教會歷史跌宕起伏,其面臨的挑戰與苦難不容遺忘。天主教會在華的境遇是自百年禁教以來,最為複雜的一個時期。與以往歷代王朝不同的是,教會此時面臨著一個崇奉無神論的政黨所建立的政權,這一政權建立起以黨統政,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一切都要在黨的完全掌控下。宗教團體本就是執政黨懷疑的對象,天主教因其特殊的背景更是被政權視為潛在的威脅,進行了多層次的監督改造。教會在這此過程中曾有過抗爭,也曾試想與政權妥協,但由於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雙方終究難以取得互信。
希望藉由這錯綜複雜的五十年(1949~2000)歷史反省,能夠讓我們從中領會到經驗教訓,適時調整與放慢腳步,聆聽聖神的引導,要相信「時間屬於祂,歷史屬於祂,光榮和權能也歸於祂,直到永遠」。
【作者序】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天主教在華歷史,可謂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教會所經歷的挑戰與困難在普世教會歷史中亦屬罕見。中國教會在政治勢力的裹挾下,艱難度日。教會領袖與信徒在無神論政權統治下,在凱撒和天主之間面臨抉擇。在堅守信仰原則或謀求生存空間這一問題上,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中國教會也出現了裂痕,兩個團體之間一度關係緊張。教會在這半世紀的時光中,在這條布滿血與淚的荊棘之路上舉步維艱,猶如基督當年所走的苦路一般。五十年來湧現出無數敢於為信仰作證的勇士,他們的勇敢與犧牲是福音精神的體現,也是中國教會能夠生存發展的精神財富。
這段歷史長久以來由於其高度的敏感性與複雜性,國內外學者少有涉及。在寫作過程中,筆者有時亦感困難重重。首先,由於中國境內環境特殊,很多檔案資料無法查閱,只有期待未來檔案解密能夠彌補本書不足;其次,許多事件當事人懾於外部環境,對於當年所經歷之事語焉不詳。這些原因影響了本書的主題研究,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本書的完成,參考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感謝。希望本書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之效。而在倉促之中,書中文字表述難免會有謬誤之處,歡迎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目錄】
第一章 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的相遇
第二章 中共宗教理念與實踐
第三章 政治運動下的天主教會
第四章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4~1959)的天主教會
第五章 階級鬥爭為綱時期(1960~1970年代)的天主教會
第六章 後文革時期的天主教會
第七章 改革開放年代的天主教會(1980~2000)
結 語
附錄一:1949~2000中國教會史大事年表
附錄二:中央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
附錄三:教宗譴責愛國會《宗徒之長》通諭(1958.06.29)
參考文獻
【內容試讀】
第一章
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的相遇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伊始,如何處理對外關係成為中共重要工作之一。天主教、基督教(新教)[ 華語世界中基督教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基督宗教泛指所有信奉耶穌基督為救主的教會涵蓋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狹義上則專指宗教改革後從天主教中分裂出的新教各派。] 這兩個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的宗教團體,被中共視為威脅政權穩定的隱患;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是中共建政初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作為一個信奉馬列主義且具有鮮明無神論色彩的政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多種宗教流傳的國度,如何鞏固起新建立的政權,考驗著中共的政治智慧。
一、共產主義對於宗教的看法
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敵視一切宗教。馬克思本人認為「宗教是顛倒了的世界觀」,「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1995),1~2頁。] 宗教與鴉片等同,一切宗教都是毒品,成為共產主義者信奉的圭臬。恩格斯在1878年《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1995),354頁。] 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宗教隨著私有制的消亡,也會自然消亡,雖然這一計畫是長期性的。宗教的作用是負面消極的。恩格斯譴責天主教會:「封建制度的巨大國際中心是羅馬天主教會。它把整個封建的西歐(儘管有各種內部的戰爭)聯合為一個大的政治體系。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 同上,390頁。] 在十九紀資產階級時代,統治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響群眾的精神手段中,第一個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 同上,401頁。]
十九世紀在歐洲基督宗教社會主義曾經流行一時,認為早期教會中的團體生活---彼此互助、財產公有---是共產主義的前驅;但馬克思、恩格斯對此強烈反對,並刻意和基督宗教社會主義劃清界限,甚至明言:「法國共產主義者最喜歡的一個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產主義。他們竭力想用聖經,用最早的基督教徒過的公社式的生活等來證明這個公式。可是這一切只是說明了,這些善良的人們絕不是最好的基督教徒,儘管他們以此自居。因為他們如果真是最好的基督教徒,那他們對聖經就會有更正確的理解,就會相信即使聖經裡有些地方可以作有利於共產主義的解釋,但是聖經的整個精神是同共產主義、同一切合理的創舉截然對立的。」[《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583頁。]
為了反駁基督教社會主義,恩格斯在1894年發表《論早期基督教歷史》,指出教會所追求完美世界是在死後的天堂,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則是追求現世的解脫,打造所謂的人間樂園,這是兩者的本質區別。為了削弱宗教的影響,必須將教會從教育和社會服務領域驅逐,取消國教,實行「政教分離」,從而加速宗教的衰落。馬克思、恩格斯對於宗教的批判,僅局限於理論層面,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建立第一個以馬克斯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俄共在其領袖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的領導下,將馬克思主義反宗教理念進一步發展,並且藉由國家機器推行嚴厲的反宗教措施,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反宗教運動。
二、蘇聯的消滅宗教實踐
蘇俄共黨首領列寧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宗教問題著作選編及講解》(北京:宗教文化,1999),155頁。] 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其世界觀是絕對的無神論,與宗教世界觀是完全對立的。要對一切宗教展開堅決鬥爭,強化無神論的宣傳,但出於革命需要,在一定時期內要利用分化宗教團體中的力量,運用統戰策略,在共產黨處於劣勢時期,要和不同宗教團體展開合作,在合作中「我們永遠要宣傳科學的世界觀,我們必須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徹底性進行鬥爭。」[ 同上,147頁。] 宗教信仰並不是個人私事,「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並不是私人的事情。我們的黨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覺悟的先進戰士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對信仰宗教這種不覺悟、無知和蒙昧的表現置之不理。對我們來說,思想鬥爭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 同上,145頁。]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列寧發展了一套比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更加激進的理論,在實踐中則是直接以國家暴力摧毀宗教。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消滅宗教的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首當其衝的就是在俄羅斯擁有悠久歷史的東正教會。
自988年基輔羅斯受洗後,斯拉夫人與東正教會形成了緊密的聯繫。尤其是沙皇俄國時期,東正教處於國教的地位,享有各種優越的條件。蘇俄政權建立後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蘇俄政權發布《土地法令》,宣布沒收「寺院、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鄉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土地將「一律無償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權,成為全民財產並交給一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譯,《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0),8頁] 取消宗教婚姻的合法性,只承認世俗婚禮的有效性。1918年1月23日,頒布《政教分離》法令,依據該法令,「教會同國家分離,每個公民都有權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戶籍工作只由民政機關,即婚姻和出生登記處辦理,剝奪過去教會所負責的事務,學校同教會分離,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不給予任何特權和津貼,凡在俄國屬於教會和宗教團體的全部財產都宣布為人民的財產,專供祈禱用的建築物和物品也只能根據地方和中央國家政權機關的特別規定,轉交有關宗教團體無償使用。」[ 同上,18~20頁。] 法令事實上剝奪了教會所有產業,含動產與不動產,使其難以在社會立足,加速其衰落。
在思想文化領域,加強無神論的宣傳,成立戰鬥的無神論組織,該組織在全國設立分支機構。列寧在1922年發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宣傳無神論思想,成立專門的雜誌,系統翻譯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來各類鼓吹無神論思想的書籍。在俄共中央成立反宗教委員會和國家與教會分離委員會,指導各地消滅宗教運動。1922年3月19日,列寧致函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中,提及展開沒收教會珍寶運動,特別指出:
我們務必通過最堅決、最迅速的方式,去沒收教會的珍寶,這樣我們才能獲得幾億盧布。為了達到某一政治目標,必須採用一系列殘酷的手段,那就應該用最堅決的方式在最短時間裡實施。我們正是應該在現在最堅決、最無情地向黑幫神職人員開戰,十分殘酷地鎮壓他們的對抗,要讓他們幾十年也忘不了。委派一名精幹的、擅長指揮全俄中央執委會成員或中央政權代表去舒亞(城市名),通過政治局五名委員給他下達口頭指示,要盡可能多地逮捕當地神職人員、小市民和城市資產階級代表,要以最快的速度審訊,審訊結束時,要槍決其中的黑幫分子……如有可能,還要槍決莫斯科和其他幾個宗教中心的黑幫分子。[〈列寧關於沒收教會珍寶致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信〉,1922年3月19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北京:社科文獻,2002),411~414頁。]
通過蘇聯檔案顯示,列寧的暴力指示非常明顯將矛頭指向一切反抗徵用教會珍寶的神職人員。所謂的教會珍寶即是歷代沙皇貴族以及百姓對與教會的捐贈,主要用於裝飾聖像、苦像及聖髑,在蘇俄共黨中央指揮下,大量教堂及修道院被劫掠摧毀,神父及修士們被流放及屠殺。1922年3月20日俄共國家政治保衛局副局長溫什利克特向政治局彙報建議:「現在逮捕東正教最高會議成員和大牧首是適時的……必須將所有強烈反對徵收財寶的神父和教徒送往饑餓的波沃爾日耶最饑餓的地區,在那裡將他們作為人民的敵人在當地饑餓的居民面前示眾。」[ 〈溫什利克特關於宗教界由於沒收教會珍品而進行活動的報告〉,1922年3月20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北京:社科文獻,2002),423頁。] 在經歷所謂獻寶運動後,從教會沒收的財寶「黃金總計442公斤,白銀336227公斤,其他貴重金屬1345公斤,重13.13克拉的鑽石33456粒,珍珠4414克,其他貴重寶石共72383塊,重28140克,硬幣20598盧布」[[俄]赫克著,高驊、楊繽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1999),72頁。]。
透過對教會產業的掠奪,使得教會一貧如洗,藉此清洗一批敢於反抗的神職人員,以反革命罪名監禁處決教會領袖。炮製「吉洪案件」[ 吉洪(Тихон,1865~1925)為當時俄羅斯東正教最高領袖,第十一任牧首。他反對蘇維埃政權對於東正教會的迫害政策,為蘇俄當局所不容,被蘇維埃政權逮捕審訊,1925年死於監禁中。他被東正教視為為信仰而死的殉道者,1989年俄羅斯東正教為其舉行了封聖典禮,尊稱其為聖吉洪。],分化東正教神職與信徒關係,扶植一批「進步神職人員」向黨中央請願,懲治教會中反蘇維埃神職與信徒,擁護蘇俄反宗教法令。這些「進步神職人員」譴責教會高層站在階級敵人的這一面,配合國際上反蘇反共的論調,譴責牧首吉洪「妄圖阻撓沒收教會珍品賑濟災民的行動,妄圖掀起民眾暴亂,扼殺與他們不共戴天的蘇維埃政權。」[《彼得格勒等地「進步神職人員」團體致俄羅斯東正教徒的呼籲書》,1922年5月10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北京:社科文獻,2002),451頁。] 他們假借教會的名義,來批鬥東正教會,這種手法,為後來很多共產政權所繼承。
三、史達林時期的宗教政策
1924年1月21日列寧去世,但是反宗教的措施並沒有終止。列寧死後,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在經歷了殘酷的黨內鬥爭後,成為新的領袖,他是蘇聯歷史上掌權最久的領導人,施政風格比列寧更加暴力殘忍,無論是席捲全俄的大清洗運動,還是對於異議人士的迫害,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1929年開始加速工業化的政策,提高鋼產量成了蘇聯各級政府的重要目標,也成了另一輪打擊宗教運動的開始,著名的砸大鐘運動拉開了序幕,各地教堂的鐘成為了掠奪的目標。當局認為教堂的鐘聲是舊時代的產物,影響了勞動人民的休息與生活,應該拆除熔煉,為國家工業化做出貢獻。
1930年開始,俄共中央政治局下令開始全面拆除教堂鐘樓,拒絕者將教堂一併拆除,僅從「謝爾吉耶夫聖三一修道院一處就獲得19口大鐘,合8165普特(130噸),熔化燭臺、枝形燭臺、神幡、洗禮盆、銅柵欄及各種裝飾物獲得約10噸有色金屬。莫斯科自1929年開始陸續封閉了30~50間教堂,每間教堂都『提供』了大量銅。比如『金屬公司』員工在1929年被關閉的大謝爾普霍夫耶穌升天教堂拆鐘14口、重達17噸;莫斯科河南岸區的聖凱薩琳教堂拆鐘21噸;1930年被關閉的阿列克西都主教教堂拆鐘10噸。」[ 厭然閒居譯,〈工廠拔地起,教堂鐘鳴息〉,2019年9月9日載於https://sanlier.blog/2019/09/09/%E5%B7%A5%E5%8E%82
%E6%8B%94%E5%9C%B0%E8%B5%B7%EF%BC%8C%E6%95%99%E5%A0%82%E9%92%9F%E9%B8%A3%E6%81%AF/] 蘇聯冶金工業部也制定五年計畫來拆除各地教堂的大鐘。蘇聯輿論也假借人民聲音,對於這場荒謬測運動大唱讚歌:
我們是最後聽過教堂鐘鳴的人。從今往後,傍晚的鐘聲、貴族的詩歌、復活節時教堂的胡言亂語、送別死者時陰森森的哀樂都將遠離我們的子孫。教會啞然,宗教入土,末了的鐘聲乃是宣告他們千年統治終結的喪鐘。而銅鐘經過無神論者冶煉廠的洗禮,也會唱起讚美勞動之響亮頌歌,機器運轉的雄偉節奏取代了昔日孱弱的祈禱鐘鳴。[ 同上。]
1926年蘇聯頒布新《刑法典》,對於宗教活動做出了嚴格限制與懲罰措施,規定任何人「在國立和私立學校中向幼年人和未成年人傳授東正教教義,或是違犯此項法律的,判處一年以下勞動改造;為教會或宗教團體的利益而強迫募捐者,判處6個月以下勞動改造或300盧布以下罰金;宗教或教會組織擅自利用行政、審判或者其他公法上的職權,和擅自行使法人權利者,判處6個月以下勞改或300盧布以下罰金;在國家或公共機關、企業中舉辦宗教儀式,或者在上述機關、企業中懸掛某種宗教畫像者,要判處3個月以下勞改或300盧布以下罰金;對以宗教信仰或其他個人信仰為藉口,拒絕或逃避服義務兵役者,要判處剝奪3年以下的自由。」[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917~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132頁。]
通過嚴刑峻法,縮小宗教生存空間,許多神職人員在無意中就觸犯了刑法而被監禁、勞改、流放。史達林執政時期,堅持拆除教堂,在首都莫斯科周邊地區,「克里姆林宮內的丘多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大教堂,幾乎『中國城』內的大部分教堂、西蒙諾夫修道院的大部分建築、紅場旁邊的契爾文斯基聖母小教堂和其他許多教堂都被搗毀。」[ 同上,134頁。] 最具代表性的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於1931年被用炸藥摧毀,並在原址上建立游泳館;這座教堂是為紀念1812年戰勝拿破崙入侵而建立,裡面收藏了大量歷史文物,這樣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教堂,最終也難逃被拆除的命運。
史達林認為拆毀教堂只是表面上消滅宗教,只有把宗教從人的思想意識中消除,才是真正的消滅宗教。神職人員與教徒是傳播宗教的主體,必須要從整體上消滅神職階層,可以借用分化方式,利用「進步神職人員」打擊所謂落後人員,待時機成熟後再一網打盡,包括「進步神職人員」也在被消滅的行列之內。在大清洗[ 11930年代,蘇共領袖史達林發動的政治清洗運動,從打擊黨內政敵,擴大到對軍隊、知識份子、黨外人士、宗教人士的大屠殺。從1936~1938年間,約有70~120萬人死於清洗運動。]之前,蘇聯一直推動內部消滅政策。1934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1934)遇刺身亡,他的死成了大清洗的導火索,為了深挖所謂階級敵人,史達林下令逮捕一批神職人員。1936年大清洗全面開展,三年內幾乎全部的主教及神父都被逮捕關押。1939年全蘇教堂數量減少三分之一,剩餘的教堂大多數也被該做倉庫廠房,用作宗教用途寥寥無幾,殘留開放的教堂僅供外國人參觀而被保留下來。[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34頁。]
殘留的東正教領袖們開始向蘇共妥協。1927年牧首謝爾蓋發表宣言,表示要做奉公守法的公民,呼籲流亡海外的俄羅斯正教會的神職與信徒承認蘇維埃政權,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壓力之下的被迫服從,縱使謝爾蓋牧首積極配合蘇聯各項活動,在大清洗中也飽受折磨,只是由於他對外代表俄羅斯東正教發言維護蘇聯當局的宗教迫害政策,才得以保全性命。其他主教們則沒有那麼幸運,35名總主教被處決或人間蒸發。彼得格勒地區神職人員1937年比1936年較少一半,由79人銳減為25人。[ 同上,156頁。]
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不僅對東正教是毀滅性的打擊,其他宗教比東正教處境更為悲慘。天主教會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被視為外國人的宗教團體,與東正教相比多了一份原罪,在反對蘇維埃政權罪名外,往往被扣上帝國主義間諜的罪名,蘇聯境內天主教全部主教們都被逮捕,流放處決,聖統制瀕於滅亡邊緣。教宗庇護十一世極為關心俄羅斯天主教信友狀況,曾經多次呼籲國際社會關心蘇聯境內宗教狀況,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廣泛回應,也讓蘇聯當局憂心忡忡。
為了挽救俄羅斯教會聖統不被滅絕,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法國耶穌會士赫爾比尼神父(Michel-Joseph Bourguignon dHerbigny,1880~1957)為主教,赴莫斯科暗中重建教會組織,赫爾比尼主教先後建立九個宗座署理區,秘密祝聖了四位主教。[ 四位主教分別為:Pie Eugène Neveu(1877~1946),法國聖母升天會會士,任命為莫斯科宗座署理,1926年4月21日秘密祝聖。Aleksander Frison(1875~1937)生於烏克蘭的德國移民後裔,1926年5月10日任命為奧德薩(Odessa)宗座署理。Boļeslavs Sloskāns(1893~1981),拉脫維亞人,1926年5月10日與Aleksander Frison一起接受主教祝聖,任命為明斯克(MInsk)宗座署理。Antoni Malecki(1861~1935),波蘭人,彼得格勒(聖彼德堡)宗座署理。] 但是在蘇聯當局殘酷的迫害政策下,幾位主教先後被逮捕驅逐,蘇聯境內天主教會一度和教廷失去聯繫。尤為悲慘的是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徒[ 1596年布列斯特會議上烏克蘭和部分白俄羅斯東正教徒改宗羅馬天主教,獲得了時任教宗克萊孟八世(Clemens VIII,1592~1605在位)批准,形成了烏克蘭希臘禮(拜占庭禮)教會,為天主教東方禮教會之一,依據2020年資料烏克蘭希臘禮信徒482萬,占烏克蘭總人口11.52%。資料來源於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Church 2020(Vatican City: Librera Editrice Vaticana, 2022)。]:在1920~1930年代的迫害中,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被流放;二戰後,1946年又被蘇聯當局強行合併與東正教,2700多所堂區被侵佔,數百萬拒絕服從的信徒轉入地下狀態。
1924年底,俄共中央委員會反宗教委員會制定蘇聯天主教條例,對天主教從組織制度、禮儀、語言、教堂的所有權,及神職人員的產生,做了嚴格的要求:「禁止天主教任何修會團體在蘇聯活動,禮儀必須用拉丁語,禁止成立慈善組織,教宗通諭及其他檔案必須由蘇聯政府審查批准後方可發行,主教和司鐸的調動要經蘇聯政府批准,蘇聯政府有權對於主教候選人進行審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反宗教委員會提出的關於蘇聯天主教基本條例草案〉,1924年12月9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卷,650頁。] 蘇共當局視羅馬為反蘇天主教精神中心,開動各種宣傳工具來反對教會;在發行的各類商品包裝上,也要印刷反宗教的宣傳,著名的宣傳有:「教士就是我們的生死仇人!用兩隻眼牢牢瞪住他要緊。讓我們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來答覆教皇的誣衊謗陷,用文化趕跑宗教和酒精。」[ 赫克著,高驊、楊繽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349頁。]
1917年十月革命前,生活在沙皇統治下的穆斯林人數近2000萬,主要生活在中亞地區。伊斯蘭教教義及法律在中亞穆斯林聚居區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建立起系統的教法學校,為穆斯林兒童提供宗教教育,這類學校實際上也扮演著教化功能,解決了穆斯林基本教育問題。十月革命後,列寧認為這類學校存在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號召黨員幹部要與這類泛伊斯蘭主義作鬥爭,關閉宗教學校。雖然黨內有人認為不應該驟然取消穆斯林宗教學校,而應開辦世俗學校與宗教學校並行,用政策鼓勵穆斯林學生進入世俗學校學習;但這一主張並沒有被黨內接納。1919年在中亞穆斯林聚居區展開了關閉宗教學校、清真寺,並沒收教產等活動,引發了穆斯林社會強烈不滿,爆發了「巴斯馬奇運動」[ 巴斯馬奇運動,是指中亞地區穆斯林為反抗蘇聯的消滅伊斯蘭教運動,而爆發的武裝反抗運動,延至1920年代末才被徹底鎮壓。]。
面對穆斯林的激烈反抗,史達林採取了支持穆斯林中的「進步分子」打擊反動穆斯林,聯共(布)中央[ 蘇聯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稱呼之一,其前身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布爾什維克派;十月革命後,1918年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1925年改稱全聯盟共產黨,簡稱聯共布;1952年聯共布十九大上,改黨名為蘇聯共產黨。]宣傳部發布關於與穆斯林宗教運動鬥爭的草案,要求採取司法懲罰與司法外的措施來鎮壓反動穆斯林宗教界,關閉穆斯林宗教學校,關閉清真寺,穆斯林教職人員被劃分為富農階級,沒收財產,流放西伯利亞地區勞改。穆斯林學校的關閉,世俗學校無法滿足眾多兒童求學問題,導致大量兒童失學。在土庫曼斯坦地區,世俗學校只能收容9%學齡兒童,整體中亞穆斯林聚居區,世俗學校只能提供15%~16%學齡兒童入學。[ 邵麗英,〈蘇聯在中亞伊斯蘭教政策的歷史嬗變〉,《中東問題研究》2017年第1期,218頁。] 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以暴力拆除清真寺,強迫穆斯林交出一切生產工具,家畜加入集體農莊。清真寺數量急劇下降,在烏茲別克地區十月革命前,清真寺數量14905座,到1936年僅剩4830座;塔什干地區不足革命前三分之一;舍拉巴茨克地區革命前有101座清真寺,到1936年則全部被摧毀。[ 同上,219頁。]
蘇聯境內的佛教徒,主要是自沙俄時代即生活在布里亞特(Buryatia)、卡爾梅克(Kalmykia)及唐努圖瓦(Tannu Tuva)三個自治共和國蒙古人的後裔,他們主要信奉藏傳佛教的格魯派。「1916年布里亞特大約34所寺院及15000名喇嘛,卡爾梅克有70所寺院及1600名喇嘛,1923年增長為2840名。在唐努圖瓦總人口6萬人中共有22所寺廟,2000名喇嘛。」[ Hans Braker, "Buddh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nihilation or Survival?”,1980年10月3日,https://biblicalstudies.org.uk/pdf/
rcl/11-1_036.pdf] 這些信奉佛教的地區在十月革命後,尚未受到反宗教運動的波及;但隨著內戰的結束及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俄共中央開始了針對佛教的打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