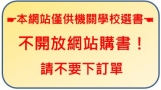曾經目光只有遠方,最後看見的卻是自己
手中地圖的邊界連結著回憶的縫隙
異域與日常,皆是存在的重量
那些遠行的人們,後來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十多年前隻身走過中東和東非,那時世界歌頌流浪,錯以為只有遠方才能聽見故事、成為故事,於是奮不顧身,說什麼都要出發。但人們幾乎不太談論從他方歸來之後,又該如何與生活共處?當遠行成為日常,停留反而需要極大勇氣。
從兩萬公里外的亞馬遜雨林到戒備森嚴的北韓,再到床底下父親遺留下來的紙箱,在一封封四十多年前的手寫信中發現那些未解的過去,以此做為線索,穿梭於過往和當下,述說一段關於此地與他方、愛與冷漠、流浪與停留的故事。
手中地圖的邊界連結著回憶的縫隙
異域與日常,皆是存在的重量
那些遠行的人們,後來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十多年前隻身走過中東和東非,那時世界歌頌流浪,錯以為只有遠方才能聽見故事、成為故事,於是奮不顧身,說什麼都要出發。但人們幾乎不太談論從他方歸來之後,又該如何與生活共處?當遠行成為日常,停留反而需要極大勇氣。
從兩萬公里外的亞馬遜雨林到戒備森嚴的北韓,再到床底下父親遺留下來的紙箱,在一封封四十多年前的手寫信中發現那些未解的過去,以此做為線索,穿梭於過往和當下,述說一段關於此地與他方、愛與冷漠、流浪與停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