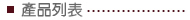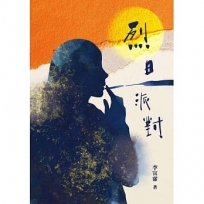【本書簡介】
烈日派對是一部女性成長小說,故事以女主角阿時追尋夢想與情感的歷程為主軸,細膩描繪她與摯友們在二十多歲這個人生階段中的迷惘、徬徨、痛苦、快樂、價值形塑以及各種體悟。小說深刻敘寫角色們在面對人生挑戰時的思索與掙扎,並探討他們與社會期待、家族期望,乃至自我認知產生衝突時,所做出的抉擇與反動。
【作者簡介】
李宜霈,一九九五年生,自認喜愛文字創作,卻到了三十歲才有一本真正的文學作品,其餘產出都獻給了語言教育。
有著認真的外表,內心卻偶爾懶散。
喜歡凝望著山與海,還有從屋簷落下的透著日光的雨水。
【作者序】
事實上,我在二十六歲結束前就已經完成《烈日派對》了,但因為一些細碎繁瑣的事、出版的困境,拖延到了年過三十的這時候,才正式要將此書付印,同時驚覺自己也已來到了和女主角阿時一樣的年紀了。我很感謝所有曾對這本書表達支持與期待的朋友:編輯部朋友、數位部朋友、公務員文官訓朋友、國高中朋友、大學朋友、英國朋友、交情或淺或深的網路筆友等,還有我的伴侶涵,以及啟蒙我寫作的高中國文老師陳雋弘老師,謝謝你們,願意耐心等候這麼多年,並不定時捎給我鼓勵的訊息,敦促我務必要將此書出版。
許多人曾問我,《烈日派對》這本書裡的故事是真實的嗎?有多少比例是真實的?我必須說,創作初始,我的確提取了我自己和我幾個朋友的人生經驗來捏塑故事雛型,因為《烈日派對》的初衷本就是描繪「二十幾歲」這個人生階段的迷惘、徬徨、痛苦、快樂、價值形塑以及各種體悟。然而,雖是由真實人生得到靈感,這些人生經驗卻經大幅度扭曲、變造、重塑、改寫,才形成《烈日派對》最終的故事,因而我會說,《烈日派對》本質上已是一本小說,裡頭的人物都是虛假的,其情節虛構比例之高已讓探究真實與否盡失意義了。我懇求、希冀任何願意拾起《烈日派對》的你,能用一雙溫柔、透明的眼睛去閱讀這個故事,若你從文字中獲得任何一絲意義或安慰,那對我來說也會是莫大的慰藉。
【內容試讀】
阿時三十歲生日那天,是個溫暖乾燥的日子,太陽很大,走在柏油路上可以看見有條清楚的界線,將陽光和陰影一分為二。光與暗,被那麼乾脆的往兩邊推開,完全沒有半點模糊餘地。
她所居住的這座城市,在冬天總是多雨濕冷,這樣溫煦明亮的日子是很難得的。在她心裡,這就像是個好預兆。事實上,她不相信預兆已經很久了,但今天對她來說是新生命的開始,她需要信仰,讓自己相信如今所選的這條路不僅是最好的決定,更是以往她走過的一切紛雜路途所交織出的解答。
不到六點她就醒來了,並再也無法入睡。即便知道自己需要休息,或許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她還是下了床,穿戴整齊,步行到三百公尺外的早餐店,買了她慣吃的翡翠抓餅和鮮奶茶。當早餐店的年邁夫妻將裝在袋裡的早餐交到她手中,並親切的向她道再見時,她心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她即將要離開這片土地,即便日後回國,也不會再回到她目前暫居的地方了──但她什麼也沒說,如常走出了早餐店,好像她明天或後天還會再光顧一般。
知道她要離開的人並不多。過去她的朋友陸續離開這個國家,前往其他地方念書或工作時,她常是那個帶頭召集大家舉行餞別宴的人。如今她自己要離開了,卻刻意的不去張揚,沒有餞別宴,也沒有一個舊地重遊的巡禮來和這片孕育她的土地告別。她可以許多方式來解釋自己的不告而別:這不是她第一次離開了、她大多數的朋友都先她一步出國了、她行程排定得太匆促了、她的身體狀況不是尚佳……但那就是一種感覺,離別越是真實,她越是不敢大聲喧嘩,彷彿害怕驚擾了還安靜蟄伏在這裡的物事,而它們的倉皇、它們的扭攪反動,都可能動搖她的決心與信仰。
她在這座城市生活了有十年之久,雖然在其中四處漂泊,每隔幾年就換一處住所,她卻感覺自己的根深深紮在這裡。當她行走在其他國度,想起所謂家鄉,腦中浮現的總是這座城市,她早已不是南方那座城市的孩子了。此番離去,或許也是十年。在後續十年間,她很可能都不會再回到這裡了。她該好好道別的,該回到自己的大學母校,在午後漫步於校園中,端詳攀附在磚瓦上的藤蔓、停放在牆邊的雜亂腳踏車,以及在紅土上就著殘餘陽光練接滾地球的學生們。她或許也該再回到新店瞧瞧,她在那裡的一間英語雜誌社待了近三年,雖然不算資歷深厚,卻已是她畢業後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了。新店也是她和她的愛人阿僅相遇的地方,在那裡的時光,可說是她生命中最充滿希望的一段歲月。
然而她從來就不是個戀舊之人,並總是排斥深入探尋自己的過去,因而最終她哪裡也沒去,悠悠忽忽的在家打點一些殘餘瑣事:把棉被寄給需要的友人、把垃圾拿到大樓回收間、把前一天穿過的睡衣收進行李箱等。幾小時進進出出的忙著,正午時分她已疲憊不堪,雙腿乏力顫抖,覺著身體似乎比平時更容易倦怠。而也再沒有什麼事情能讓她保持忙碌,從此刻複雜的情緒裡分神了,於是她強迫自己回到床上再休息一會兒。
躺在已經剝除了床單的潔白床墊上,阿時無可避免的失去了晨起時感覺到的希望,沉入如深邃潭水般的空虛之中。在去加拿大這件事上,曾有無數人對她說過要和她一同啟程,一直以來她疑惑著最終那人究竟是誰。她沒有預見到,這天來臨時,她竟是要獨自一人面對。
她的遠房表弟阿予在下午五點從板橋來到她寄居的地方,陪她前往機場。見到她時,阿予學醫的直覺讓他得以察覺出阿時似乎有些不對勁,但他也說不上是哪裡不對勁,只覺得她看起來氣色糟透了。下樓的時候,阿予替阿時拿那只大的行李箱,她自己拿那只小的。電梯抵達一樓時,阿時想起要將鑰匙還回去,於是讓阿予先帶著行李到社區門口攔計程車,自己則繞到設置信箱的小間。
將大門鑰匙投入信箱時,鑰匙落入信箱底部的那聲喀拉就像尖刺,刺痛阿時的腹部,但她沒有再回頭多看一眼,就離開了這個她住了超過一年的家,彷彿懼怕著童話故事所說的,一旦回頭就永遠無法離開了。而她的確想離開,她也必須離開。
在去機場的客運上,阿時心有旁騖的和阿予聊起他的工作。阿予告訴她,他這一年來陸續在準備學士後醫考試,但正職工作太過繁忙,讓他無法專心備考,因此他計畫在不久後辭掉生醫研究工作,全心準備考試。阿時感到愕然──又一個人放棄了學術,又一個人放棄了出國生活,這些年來,她原本堅定走在學術路上的友人們,都紛紛放棄、紛紛退出了。坐在阿予身邊,阿時感到益發孤單,數分鐘後,她才意識到這份孤單更多是因為她體認到自己不再是阿予的密友了,阿予就這麼獨立做出了決定,他再也不會把自己最祕密的心路歷程悉數向她透露了。
兩人沉默了些時候,阿予又說,「之後,我應該也會搬回屏東老家去吧,臺北的房租太貴了,而且現在你也要離開這裡了,我留在臺北的理由又少一個了,不如回家去吧。」
他說這些話時,幾乎不帶任何情緒,可那句現在你也要離開這裡了,卻在阿時心中掀起波瀾。
她仔仔細細的看著阿予,他上月底剛滿二十九歲,眼尾已有了細微的紋路,雖然非常、非常細微,需要像是這樣緊緊挨著彼此才看得到,但終究還是紋路,是衰老的象徵。奇怪的是,在意識到他們即將失去青春年華、即將不可逆的快速老去之時,阿時卻記起了阿予十九歲時的樣子,記起了他剛上大學時,參加社團博覽會,和當時是社長的她一塊坐在椰子樹下草坪閒聊,進而發現彼此竟是六等親表姐弟、小時候還曾一起住在同個社區,沒想到竟在大學重逢。那一刻,阿予露出驚喜燦爛的笑容,那是阿時見過最近似於陽光的金黃閃耀笑靨了。那笑靨深刻烙印在她腦中。
阿予或許是她離開這片土地時唯一放不下的人了,見到他之前,阿時在心中構思了許多必須對他說的話,最後卻一句都沒有說出來,只祝福他平安順利,然後兩人的話題就轉移到她在加拿大的規畫上頭了。
到機場之後,阿予陪著阿時在入境大廳坐了好一會兒。數年前他們一起去阿拉斯加看極光時,也是這樣肩並肩坐在機場裡面等候。當時他們坐在這裡所聊的情感之事,都已然成為過往雲煙,他們口中的那些人,如今也早已不在他們生命裡了。
阿時轉頭看向一旁來來去去的旅人,還有那些舉著字牌等候親友的人們,那景象和數年前並無太大分別。而這數十年如一日的景象卻讓她感慨起自己生命其餘部分的物是人非,覺得如今她和阿予再度坐在這裡,心境與信仰都和過往有很大的不同了。
該要分別的時候,阿時抱了抱阿予,抱得有些彆扭,因為直到這一刻她都還在掙扎是否要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最後她選擇沉默,什麼也沒多說就向阿予道別了。反倒是阿予,不知是想要打破沉默或是想要延緩離別,又突然想起似的提到自己考完試後,若有些空閒,會去加拿大拜訪阿時。
在三樓出境大廳的看臺上,阿時望著阿予行過一樓入境大廳的身影。在顏色紛雜的人群中,逐漸遠去的阿予成了一個不清晰的小點。那熟悉的滄海一粟的渺茫感,在此時又襲上阿時心頭,讓她覺得一切都沒什麼要緊了,因為人在這偌大的宇宙中,不過是一粒塵埃般的存在,很多人們認為自己該做或不該做的事,不過都是源自人為建構的虛浮框架罷了。做和不做,這樣在當下看來天差地遠的決定,宏觀而言實則都無足輕重。於是她像終於卸下長久以來駝著的包袱似的,別過頭,離開了那可以望見阿予的地方。而阿予在出自動玻璃門之前,又回頭朝阿時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卻發現她已經離開了。「也可能只是我沒能在人海中找到她吧。」他在心裡這麼想著,轉身步出了機場。
飛機起飛時,夜已深了。吃過第一餐後,阿時就昏睡了過去,期間只短暫醒來過一次,將遮光板拉開一小縫,瞥見窗外一片闃黑。機組人員第二次送餐時,她因太過疲累而毫無知覺,旁邊的年輕女子好心的把她叫起來。阿時轉頭向她道謝,這才發現那女子身旁坐的是一位金髮、白皮膚、有著西方面孔的男人,他和那年輕女子看起來應該是一對愛侶。空服員問餐時,那男人輕聲在妻子或女友耳邊翻譯空服員所說的話,而那女子溫柔的替他調整毛毯、擦去他面頰上的毛屑。
這溫馨的景象,卻像酸液一樣腐蝕阿時的五臟六腑。並不是因為嫉妒,她對愛情早已不抱希望。難受是因為,此情此景正是她年輕時書寫的其中一本小說的最後場景,小說未了,但帶給她靈感的人離開了,她也不再對文學懷抱信心,故事就這樣停留在男女主角處於一萬公尺高的那一刻,從來沒有抵達溫哥華。
不再對文學懷抱信心,那大抵是阿時經歷過最悲涼的事情之一了。十幾二十幾歲時,文學對她而言就是信仰。她所走過的一切迂迴路途,所受過的痛苦磨難,她相信,只要能轉化為文字結晶,讓他人讀了之後產生共鳴、感到寬慰,那些荒誕就不算白走一遭,而她也能透過鐫刻文字讓一部分的自己永存於世。然而,當她拿著自己的作品,被所有她能聯繫得上的出版社以各式理由拒絕時,她不得不接受那殘酷的現實:如今早已不是實體書籍、文學出版的時代了,也不是她的時代,或許任何時候都不是,又有誰會在乎她寫下的任何東西呢?夢醒之初,阿時陷入一段悠長的惶惑與絕望裡,認為自己活在世上根本毫無意義。後來,她逐漸與文學形同陌路,不再書寫文學了,甚至也不再閱讀文學,轉而將心力投注在工作與研究之上,才重新找回一點自己的價值。
而今再次想起來又是為了什麼呢?阿時覺得荒謬無比。她伸手到座位底下的背包裡,拿出電腦,打開資料夾,將小說一本、一本拖進資源回收筒,就像在進行什麼嚴酷的行刑。輪到那個未能抵達溫哥華的故事時,阿時卻半途猶豫了──檔案被拖曳到半空中,懸盪了十數秒之久──而後,阿時還是狠下心來,將它丟進資源回收筒,並按下永久刪除。「再見了,」阿時輕聲在心裡說,「再見了一切。」再見了,年輕時曾是文字工作者的自己;再見了,年輕時曾信仰文學的自己;再見了,年輕時曾經奮力向前奔跑、自認能夠留下些文字的自己。
永久刪除過去所寫下的一切之後,那些回憶、那些她所走過的路,卻反倒像荒漠久違滲出的細流般,湧上她心頭。在離地一萬尺的密閉機艙裡,世事彷彿都遙不可及,時間彷彿都沒了意義,阿時這才得以停下來,重新審視她所走過的路途,並感覺到告別這一切所帶來的情緒。
烈日派對是一部女性成長小說,故事以女主角阿時追尋夢想與情感的歷程為主軸,細膩描繪她與摯友們在二十多歲這個人生階段中的迷惘、徬徨、痛苦、快樂、價值形塑以及各種體悟。小說深刻敘寫角色們在面對人生挑戰時的思索與掙扎,並探討他們與社會期待、家族期望,乃至自我認知產生衝突時,所做出的抉擇與反動。
【作者簡介】
李宜霈,一九九五年生,自認喜愛文字創作,卻到了三十歲才有一本真正的文學作品,其餘產出都獻給了語言教育。
有著認真的外表,內心卻偶爾懶散。
喜歡凝望著山與海,還有從屋簷落下的透著日光的雨水。
【作者序】
事實上,我在二十六歲結束前就已經完成《烈日派對》了,但因為一些細碎繁瑣的事、出版的困境,拖延到了年過三十的這時候,才正式要將此書付印,同時驚覺自己也已來到了和女主角阿時一樣的年紀了。我很感謝所有曾對這本書表達支持與期待的朋友:編輯部朋友、數位部朋友、公務員文官訓朋友、國高中朋友、大學朋友、英國朋友、交情或淺或深的網路筆友等,還有我的伴侶涵,以及啟蒙我寫作的高中國文老師陳雋弘老師,謝謝你們,願意耐心等候這麼多年,並不定時捎給我鼓勵的訊息,敦促我務必要將此書出版。
許多人曾問我,《烈日派對》這本書裡的故事是真實的嗎?有多少比例是真實的?我必須說,創作初始,我的確提取了我自己和我幾個朋友的人生經驗來捏塑故事雛型,因為《烈日派對》的初衷本就是描繪「二十幾歲」這個人生階段的迷惘、徬徨、痛苦、快樂、價值形塑以及各種體悟。然而,雖是由真實人生得到靈感,這些人生經驗卻經大幅度扭曲、變造、重塑、改寫,才形成《烈日派對》最終的故事,因而我會說,《烈日派對》本質上已是一本小說,裡頭的人物都是虛假的,其情節虛構比例之高已讓探究真實與否盡失意義了。我懇求、希冀任何願意拾起《烈日派對》的你,能用一雙溫柔、透明的眼睛去閱讀這個故事,若你從文字中獲得任何一絲意義或安慰,那對我來說也會是莫大的慰藉。
【內容試讀】
阿時三十歲生日那天,是個溫暖乾燥的日子,太陽很大,走在柏油路上可以看見有條清楚的界線,將陽光和陰影一分為二。光與暗,被那麼乾脆的往兩邊推開,完全沒有半點模糊餘地。
她所居住的這座城市,在冬天總是多雨濕冷,這樣溫煦明亮的日子是很難得的。在她心裡,這就像是個好預兆。事實上,她不相信預兆已經很久了,但今天對她來說是新生命的開始,她需要信仰,讓自己相信如今所選的這條路不僅是最好的決定,更是以往她走過的一切紛雜路途所交織出的解答。
不到六點她就醒來了,並再也無法入睡。即便知道自己需要休息,或許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她還是下了床,穿戴整齊,步行到三百公尺外的早餐店,買了她慣吃的翡翠抓餅和鮮奶茶。當早餐店的年邁夫妻將裝在袋裡的早餐交到她手中,並親切的向她道再見時,她心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她即將要離開這片土地,即便日後回國,也不會再回到她目前暫居的地方了──但她什麼也沒說,如常走出了早餐店,好像她明天或後天還會再光顧一般。
知道她要離開的人並不多。過去她的朋友陸續離開這個國家,前往其他地方念書或工作時,她常是那個帶頭召集大家舉行餞別宴的人。如今她自己要離開了,卻刻意的不去張揚,沒有餞別宴,也沒有一個舊地重遊的巡禮來和這片孕育她的土地告別。她可以許多方式來解釋自己的不告而別:這不是她第一次離開了、她大多數的朋友都先她一步出國了、她行程排定得太匆促了、她的身體狀況不是尚佳……但那就是一種感覺,離別越是真實,她越是不敢大聲喧嘩,彷彿害怕驚擾了還安靜蟄伏在這裡的物事,而它們的倉皇、它們的扭攪反動,都可能動搖她的決心與信仰。
她在這座城市生活了有十年之久,雖然在其中四處漂泊,每隔幾年就換一處住所,她卻感覺自己的根深深紮在這裡。當她行走在其他國度,想起所謂家鄉,腦中浮現的總是這座城市,她早已不是南方那座城市的孩子了。此番離去,或許也是十年。在後續十年間,她很可能都不會再回到這裡了。她該好好道別的,該回到自己的大學母校,在午後漫步於校園中,端詳攀附在磚瓦上的藤蔓、停放在牆邊的雜亂腳踏車,以及在紅土上就著殘餘陽光練接滾地球的學生們。她或許也該再回到新店瞧瞧,她在那裡的一間英語雜誌社待了近三年,雖然不算資歷深厚,卻已是她畢業後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了。新店也是她和她的愛人阿僅相遇的地方,在那裡的時光,可說是她生命中最充滿希望的一段歲月。
然而她從來就不是個戀舊之人,並總是排斥深入探尋自己的過去,因而最終她哪裡也沒去,悠悠忽忽的在家打點一些殘餘瑣事:把棉被寄給需要的友人、把垃圾拿到大樓回收間、把前一天穿過的睡衣收進行李箱等。幾小時進進出出的忙著,正午時分她已疲憊不堪,雙腿乏力顫抖,覺著身體似乎比平時更容易倦怠。而也再沒有什麼事情能讓她保持忙碌,從此刻複雜的情緒裡分神了,於是她強迫自己回到床上再休息一會兒。
躺在已經剝除了床單的潔白床墊上,阿時無可避免的失去了晨起時感覺到的希望,沉入如深邃潭水般的空虛之中。在去加拿大這件事上,曾有無數人對她說過要和她一同啟程,一直以來她疑惑著最終那人究竟是誰。她沒有預見到,這天來臨時,她竟是要獨自一人面對。
她的遠房表弟阿予在下午五點從板橋來到她寄居的地方,陪她前往機場。見到她時,阿予學醫的直覺讓他得以察覺出阿時似乎有些不對勁,但他也說不上是哪裡不對勁,只覺得她看起來氣色糟透了。下樓的時候,阿予替阿時拿那只大的行李箱,她自己拿那只小的。電梯抵達一樓時,阿時想起要將鑰匙還回去,於是讓阿予先帶著行李到社區門口攔計程車,自己則繞到設置信箱的小間。
將大門鑰匙投入信箱時,鑰匙落入信箱底部的那聲喀拉就像尖刺,刺痛阿時的腹部,但她沒有再回頭多看一眼,就離開了這個她住了超過一年的家,彷彿懼怕著童話故事所說的,一旦回頭就永遠無法離開了。而她的確想離開,她也必須離開。
在去機場的客運上,阿時心有旁騖的和阿予聊起他的工作。阿予告訴她,他這一年來陸續在準備學士後醫考試,但正職工作太過繁忙,讓他無法專心備考,因此他計畫在不久後辭掉生醫研究工作,全心準備考試。阿時感到愕然──又一個人放棄了學術,又一個人放棄了出國生活,這些年來,她原本堅定走在學術路上的友人們,都紛紛放棄、紛紛退出了。坐在阿予身邊,阿時感到益發孤單,數分鐘後,她才意識到這份孤單更多是因為她體認到自己不再是阿予的密友了,阿予就這麼獨立做出了決定,他再也不會把自己最祕密的心路歷程悉數向她透露了。
兩人沉默了些時候,阿予又說,「之後,我應該也會搬回屏東老家去吧,臺北的房租太貴了,而且現在你也要離開這裡了,我留在臺北的理由又少一個了,不如回家去吧。」
他說這些話時,幾乎不帶任何情緒,可那句現在你也要離開這裡了,卻在阿時心中掀起波瀾。
她仔仔細細的看著阿予,他上月底剛滿二十九歲,眼尾已有了細微的紋路,雖然非常、非常細微,需要像是這樣緊緊挨著彼此才看得到,但終究還是紋路,是衰老的象徵。奇怪的是,在意識到他們即將失去青春年華、即將不可逆的快速老去之時,阿時卻記起了阿予十九歲時的樣子,記起了他剛上大學時,參加社團博覽會,和當時是社長的她一塊坐在椰子樹下草坪閒聊,進而發現彼此竟是六等親表姐弟、小時候還曾一起住在同個社區,沒想到竟在大學重逢。那一刻,阿予露出驚喜燦爛的笑容,那是阿時見過最近似於陽光的金黃閃耀笑靨了。那笑靨深刻烙印在她腦中。
阿予或許是她離開這片土地時唯一放不下的人了,見到他之前,阿時在心中構思了許多必須對他說的話,最後卻一句都沒有說出來,只祝福他平安順利,然後兩人的話題就轉移到她在加拿大的規畫上頭了。
到機場之後,阿予陪著阿時在入境大廳坐了好一會兒。數年前他們一起去阿拉斯加看極光時,也是這樣肩並肩坐在機場裡面等候。當時他們坐在這裡所聊的情感之事,都已然成為過往雲煙,他們口中的那些人,如今也早已不在他們生命裡了。
阿時轉頭看向一旁來來去去的旅人,還有那些舉著字牌等候親友的人們,那景象和數年前並無太大分別。而這數十年如一日的景象卻讓她感慨起自己生命其餘部分的物是人非,覺得如今她和阿予再度坐在這裡,心境與信仰都和過往有很大的不同了。
該要分別的時候,阿時抱了抱阿予,抱得有些彆扭,因為直到這一刻她都還在掙扎是否要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最後她選擇沉默,什麼也沒多說就向阿予道別了。反倒是阿予,不知是想要打破沉默或是想要延緩離別,又突然想起似的提到自己考完試後,若有些空閒,會去加拿大拜訪阿時。
在三樓出境大廳的看臺上,阿時望著阿予行過一樓入境大廳的身影。在顏色紛雜的人群中,逐漸遠去的阿予成了一個不清晰的小點。那熟悉的滄海一粟的渺茫感,在此時又襲上阿時心頭,讓她覺得一切都沒什麼要緊了,因為人在這偌大的宇宙中,不過是一粒塵埃般的存在,很多人們認為自己該做或不該做的事,不過都是源自人為建構的虛浮框架罷了。做和不做,這樣在當下看來天差地遠的決定,宏觀而言實則都無足輕重。於是她像終於卸下長久以來駝著的包袱似的,別過頭,離開了那可以望見阿予的地方。而阿予在出自動玻璃門之前,又回頭朝阿時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卻發現她已經離開了。「也可能只是我沒能在人海中找到她吧。」他在心裡這麼想著,轉身步出了機場。
飛機起飛時,夜已深了。吃過第一餐後,阿時就昏睡了過去,期間只短暫醒來過一次,將遮光板拉開一小縫,瞥見窗外一片闃黑。機組人員第二次送餐時,她因太過疲累而毫無知覺,旁邊的年輕女子好心的把她叫起來。阿時轉頭向她道謝,這才發現那女子身旁坐的是一位金髮、白皮膚、有著西方面孔的男人,他和那年輕女子看起來應該是一對愛侶。空服員問餐時,那男人輕聲在妻子或女友耳邊翻譯空服員所說的話,而那女子溫柔的替他調整毛毯、擦去他面頰上的毛屑。
這溫馨的景象,卻像酸液一樣腐蝕阿時的五臟六腑。並不是因為嫉妒,她對愛情早已不抱希望。難受是因為,此情此景正是她年輕時書寫的其中一本小說的最後場景,小說未了,但帶給她靈感的人離開了,她也不再對文學懷抱信心,故事就這樣停留在男女主角處於一萬公尺高的那一刻,從來沒有抵達溫哥華。
不再對文學懷抱信心,那大抵是阿時經歷過最悲涼的事情之一了。十幾二十幾歲時,文學對她而言就是信仰。她所走過的一切迂迴路途,所受過的痛苦磨難,她相信,只要能轉化為文字結晶,讓他人讀了之後產生共鳴、感到寬慰,那些荒誕就不算白走一遭,而她也能透過鐫刻文字讓一部分的自己永存於世。然而,當她拿著自己的作品,被所有她能聯繫得上的出版社以各式理由拒絕時,她不得不接受那殘酷的現實:如今早已不是實體書籍、文學出版的時代了,也不是她的時代,或許任何時候都不是,又有誰會在乎她寫下的任何東西呢?夢醒之初,阿時陷入一段悠長的惶惑與絕望裡,認為自己活在世上根本毫無意義。後來,她逐漸與文學形同陌路,不再書寫文學了,甚至也不再閱讀文學,轉而將心力投注在工作與研究之上,才重新找回一點自己的價值。
而今再次想起來又是為了什麼呢?阿時覺得荒謬無比。她伸手到座位底下的背包裡,拿出電腦,打開資料夾,將小說一本、一本拖進資源回收筒,就像在進行什麼嚴酷的行刑。輪到那個未能抵達溫哥華的故事時,阿時卻半途猶豫了──檔案被拖曳到半空中,懸盪了十數秒之久──而後,阿時還是狠下心來,將它丟進資源回收筒,並按下永久刪除。「再見了,」阿時輕聲在心裡說,「再見了一切。」再見了,年輕時曾是文字工作者的自己;再見了,年輕時曾信仰文學的自己;再見了,年輕時曾經奮力向前奔跑、自認能夠留下些文字的自己。
永久刪除過去所寫下的一切之後,那些回憶、那些她所走過的路,卻反倒像荒漠久違滲出的細流般,湧上她心頭。在離地一萬尺的密閉機艙裡,世事彷彿都遙不可及,時間彷彿都沒了意義,阿時這才得以停下來,重新審視她所走過的路途,並感覺到告別這一切所帶來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