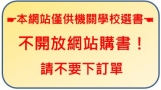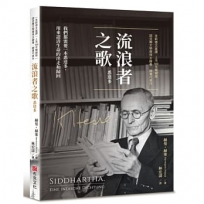流浪者之歌(悉達多)|全新德文直譯|上市100年暢銷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曼.赫塞代表作。我們都需要一本悉達多,用來認清生命的出走和歸回
出版社:布克文化
出版日期:2025-08-12
語言:中文
ISBN:9786267672747
裝訂:平裝
定價:350 元
|全新德文直譯|上市100年暢銷版|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曼.赫塞代表作。
譯成60多國語言,
影響超過1.4億人!
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悉達多)》自1922年問世以來,被譽為心靈成長與自我覺醒的經典之作,跨越百年仍深深影響無數讀者與思想家。
學習禪定──
悉達多以禪定觀想把蒼鷺攝入他的靈魂,飛越叢林群山,他就是蒼鷺,吃魚,宛如蒼鷺一樣挨餓,說話就像蒼鷺的鳴囀,也和蒼鷺一樣死亡……
遇見佛陀──
佛陀行步平安庠序,心不外馳,神情無喜亦無憂,看似含笑不語,寂靜、安穩,身著壞色衣,步伐不疾不徐,他默默慈眼垂視,他默默垂下的手,默默下垂的手指,都在訴說著和平,訴說著圓滿……
覺醒──
就在那一彈指間,他也豁然心開意解:他,其實就像一個醒覺者或者新生者一樣,他必須重新開始他的生活,整個從頭來過,走在回到自己的路上……
入世輪迴──
世俗擄獲了他,愛欲、染著、懶惰和貪婪……染上了最後一個也是最墮落的癮癖,賭博──他肆無忌憚地下大注,憎恨他自己,嘲弄他自己,一擲千金,千金散盡,輸掉、贏回來又輸掉。如是周而復始中,他漸漸累了,漸漸老了,漸漸病了……
在河畔──
他從來沒有這麼喜歡一條河,他從來不知道流水的聲音和寓意如此的強烈而美麗。他覺得河流似乎要對他訴說什麼特別的事物,他還不明白的事物,一直在等候著他的事物──新的悉達多深深愛上了這條洹洹河流……
唵──
有個認知漸漸萌芽、漸漸成熟,認識到真正的智慧究竟是什麼……,所有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同時現前,一切都是殊勝的,完美的……
赫曼.赫塞的印度詩篇:「我的印度故事,我的獵鷹,我的太陽花──」
【譯序】赫曼.赫塞與悉達多
(節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動筆寫作《流浪者之歌》,當時他和第一任妻子瑪利亞.貝努利(Maria Bernoulli)陷入困境,一方面是妻子患有思覺失調症,另一方面赫塞的藝術家角色也無法勝任中產階級一家之長的任務。(注1)
當他埋首寫作的那段日子裡,瑪利亞暫時住在精神療養院,而他們的三個兒子則寄宿在親戚家裡,赫塞自己也從伯恩(Bern)搬到提辛(Tessin, Ticino)獨居,在那裡住了十二年。他回憶往昔,覺得當時經濟拮据而孤單的他經歷了一段「最充實、最豐足、最勤奮也最燦爛的」日子(注2),也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了舉世聞名的《徬徨少年時》(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 Fischer Verlag, 1919)。
赫塞為《流浪者之歌》做了大量研究和筆記,很快就寫成了第一部以及第二部的前幾章,可是寫到了〈在河畔〉的時候卻遇到了瓶頸,這筆一擱就是一年半,其間當然不是無所事事,他寫了許多小品、序言和散文。他在一九二○年的一則日記裡寫道:
「我的印度故事,我的獵鷹,我的太陽花,主角悉達多,在一個失敗的章節裡已經中斷了好幾個月了──我還記得那一天,我看到故事寫不下去了,我在等待注入什麼新的東西!它的開頭如此美麗,它的開展如此筆直,而它卻戛然而止!這類的情況,批評家和傳記作家會說,那是因為江郎才盡,筆下疲軟,或者是馳騁外物──你們隨便找一本歌德的傳記,翻閱一下裡頭白痴的評注就知道了!
「我的情況很簡單,也不難解釋。在我的印度故事裡,但凡寫到我真正經歷過的故事,總是揮灑自如:年輕婆羅門求道時的心境,他折磨自己,刻苦修行,持戒忍辱,卻認識到那是至道的障礙。當我寫到悉達多捨棄種種苦行,那個持守苦行的悉達多,現在要把他寫成一個勝利者、寫成一個阿世媚俗的人,寫成一個征服者,我就寫不下去了。──可是我會往下寫的,遲早有一天,而他也會變成一個勝利者。」(注3)
「《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於一九一九年冬天動筆,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間,寫作則相隔了一年半。那時候──並沒有第一次那麼自然,但是比任何一次都更加強烈的──感覺到,要寫自己沒有親身親歷到的東西,那是一件荒謬的事。在擱下《流浪者之歌》的寫作的那段日子裡,必須惡補一點苦行和靜慮思惟的生活,才能真正重溫我自青少年就熟稔的印度神聖心靈。由於我並沒有像一個皈依者堅持他選擇的宗教那樣堅守著這個世界,而是不時離開這個世界,而在《流浪者之歌》之後,又創作了《荒野之狼》(Der Steppenwolf),那些喜歡《流浪者之歌》而又沒有真正讀懂《荒野之狼》的讀者們,時常深感惋惜而對我頗有微辭。對於那些指責,我並沒有加以回應,我之忠於《荒野之狼》正如我忠於《流浪者之歌》;對於我而言,我的人生和我的作品一樣,都是個獨立的整體,我不覺得有必要特意去證明或辯護什麼。」(Der Weg nach Innen)
自一九一六年,赫曼.赫塞因憂鬱症而找到榮格的學生──朗恩醫師(Josef Bernhard Lang)──接受心理治療。一九二一年六月,赫塞更接受榮格的諮商治療。讓他踏上了找尋自我的另一條道路。此外,研讀老子的《道德經》也對接下來的小說寫作產生重大的影響。一九二二年三月,赫塞重新執筆,於五月初完成整部小說,並於同年十月出版。(注4)
這次的譯本依據收錄於《赫塞全集》的《流浪者之歌》(Hermann Hesse.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Band 5, Suhrkamp Verlag, 1987, S. 355-471)譯出,部分句子和一九二二年的版本(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Fischer, Berlin 1922.)略有出入,在翻譯過程中則視上下文予以保留或者是加以修改。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曼.赫塞代表作。
譯成60多國語言,
影響超過1.4億人!
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悉達多)》自1922年問世以來,被譽為心靈成長與自我覺醒的經典之作,跨越百年仍深深影響無數讀者與思想家。
學習禪定──
悉達多以禪定觀想把蒼鷺攝入他的靈魂,飛越叢林群山,他就是蒼鷺,吃魚,宛如蒼鷺一樣挨餓,說話就像蒼鷺的鳴囀,也和蒼鷺一樣死亡……
遇見佛陀──
佛陀行步平安庠序,心不外馳,神情無喜亦無憂,看似含笑不語,寂靜、安穩,身著壞色衣,步伐不疾不徐,他默默慈眼垂視,他默默垂下的手,默默下垂的手指,都在訴說著和平,訴說著圓滿……
覺醒──
就在那一彈指間,他也豁然心開意解:他,其實就像一個醒覺者或者新生者一樣,他必須重新開始他的生活,整個從頭來過,走在回到自己的路上……
入世輪迴──
世俗擄獲了他,愛欲、染著、懶惰和貪婪……染上了最後一個也是最墮落的癮癖,賭博──他肆無忌憚地下大注,憎恨他自己,嘲弄他自己,一擲千金,千金散盡,輸掉、贏回來又輸掉。如是周而復始中,他漸漸累了,漸漸老了,漸漸病了……
在河畔──
他從來沒有這麼喜歡一條河,他從來不知道流水的聲音和寓意如此的強烈而美麗。他覺得河流似乎要對他訴說什麼特別的事物,他還不明白的事物,一直在等候著他的事物──新的悉達多深深愛上了這條洹洹河流……
唵──
有個認知漸漸萌芽、漸漸成熟,認識到真正的智慧究竟是什麼……,所有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同時現前,一切都是殊勝的,完美的……
赫曼.赫塞的印度詩篇:「我的印度故事,我的獵鷹,我的太陽花──」
【譯序】赫曼.赫塞與悉達多
(節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動筆寫作《流浪者之歌》,當時他和第一任妻子瑪利亞.貝努利(Maria Bernoulli)陷入困境,一方面是妻子患有思覺失調症,另一方面赫塞的藝術家角色也無法勝任中產階級一家之長的任務。(注1)
當他埋首寫作的那段日子裡,瑪利亞暫時住在精神療養院,而他們的三個兒子則寄宿在親戚家裡,赫塞自己也從伯恩(Bern)搬到提辛(Tessin, Ticino)獨居,在那裡住了十二年。他回憶往昔,覺得當時經濟拮据而孤單的他經歷了一段「最充實、最豐足、最勤奮也最燦爛的」日子(注2),也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了舉世聞名的《徬徨少年時》(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 Fischer Verlag, 1919)。
赫塞為《流浪者之歌》做了大量研究和筆記,很快就寫成了第一部以及第二部的前幾章,可是寫到了〈在河畔〉的時候卻遇到了瓶頸,這筆一擱就是一年半,其間當然不是無所事事,他寫了許多小品、序言和散文。他在一九二○年的一則日記裡寫道:
「我的印度故事,我的獵鷹,我的太陽花,主角悉達多,在一個失敗的章節裡已經中斷了好幾個月了──我還記得那一天,我看到故事寫不下去了,我在等待注入什麼新的東西!它的開頭如此美麗,它的開展如此筆直,而它卻戛然而止!這類的情況,批評家和傳記作家會說,那是因為江郎才盡,筆下疲軟,或者是馳騁外物──你們隨便找一本歌德的傳記,翻閱一下裡頭白痴的評注就知道了!
「我的情況很簡單,也不難解釋。在我的印度故事裡,但凡寫到我真正經歷過的故事,總是揮灑自如:年輕婆羅門求道時的心境,他折磨自己,刻苦修行,持戒忍辱,卻認識到那是至道的障礙。當我寫到悉達多捨棄種種苦行,那個持守苦行的悉達多,現在要把他寫成一個勝利者、寫成一個阿世媚俗的人,寫成一個征服者,我就寫不下去了。──可是我會往下寫的,遲早有一天,而他也會變成一個勝利者。」(注3)
「《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於一九一九年冬天動筆,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間,寫作則相隔了一年半。那時候──並沒有第一次那麼自然,但是比任何一次都更加強烈的──感覺到,要寫自己沒有親身親歷到的東西,那是一件荒謬的事。在擱下《流浪者之歌》的寫作的那段日子裡,必須惡補一點苦行和靜慮思惟的生活,才能真正重溫我自青少年就熟稔的印度神聖心靈。由於我並沒有像一個皈依者堅持他選擇的宗教那樣堅守著這個世界,而是不時離開這個世界,而在《流浪者之歌》之後,又創作了《荒野之狼》(Der Steppenwolf),那些喜歡《流浪者之歌》而又沒有真正讀懂《荒野之狼》的讀者們,時常深感惋惜而對我頗有微辭。對於那些指責,我並沒有加以回應,我之忠於《荒野之狼》正如我忠於《流浪者之歌》;對於我而言,我的人生和我的作品一樣,都是個獨立的整體,我不覺得有必要特意去證明或辯護什麼。」(Der Weg nach Innen)
自一九一六年,赫曼.赫塞因憂鬱症而找到榮格的學生──朗恩醫師(Josef Bernhard Lang)──接受心理治療。一九二一年六月,赫塞更接受榮格的諮商治療。讓他踏上了找尋自我的另一條道路。此外,研讀老子的《道德經》也對接下來的小說寫作產生重大的影響。一九二二年三月,赫塞重新執筆,於五月初完成整部小說,並於同年十月出版。(注4)
這次的譯本依據收錄於《赫塞全集》的《流浪者之歌》(Hermann Hesse.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Band 5, Suhrkamp Verlag, 1987, S. 355-471)譯出,部分句子和一九二二年的版本(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Fischer, Berlin 1922.)略有出入,在翻譯過程中則視上下文予以保留或者是加以修改。